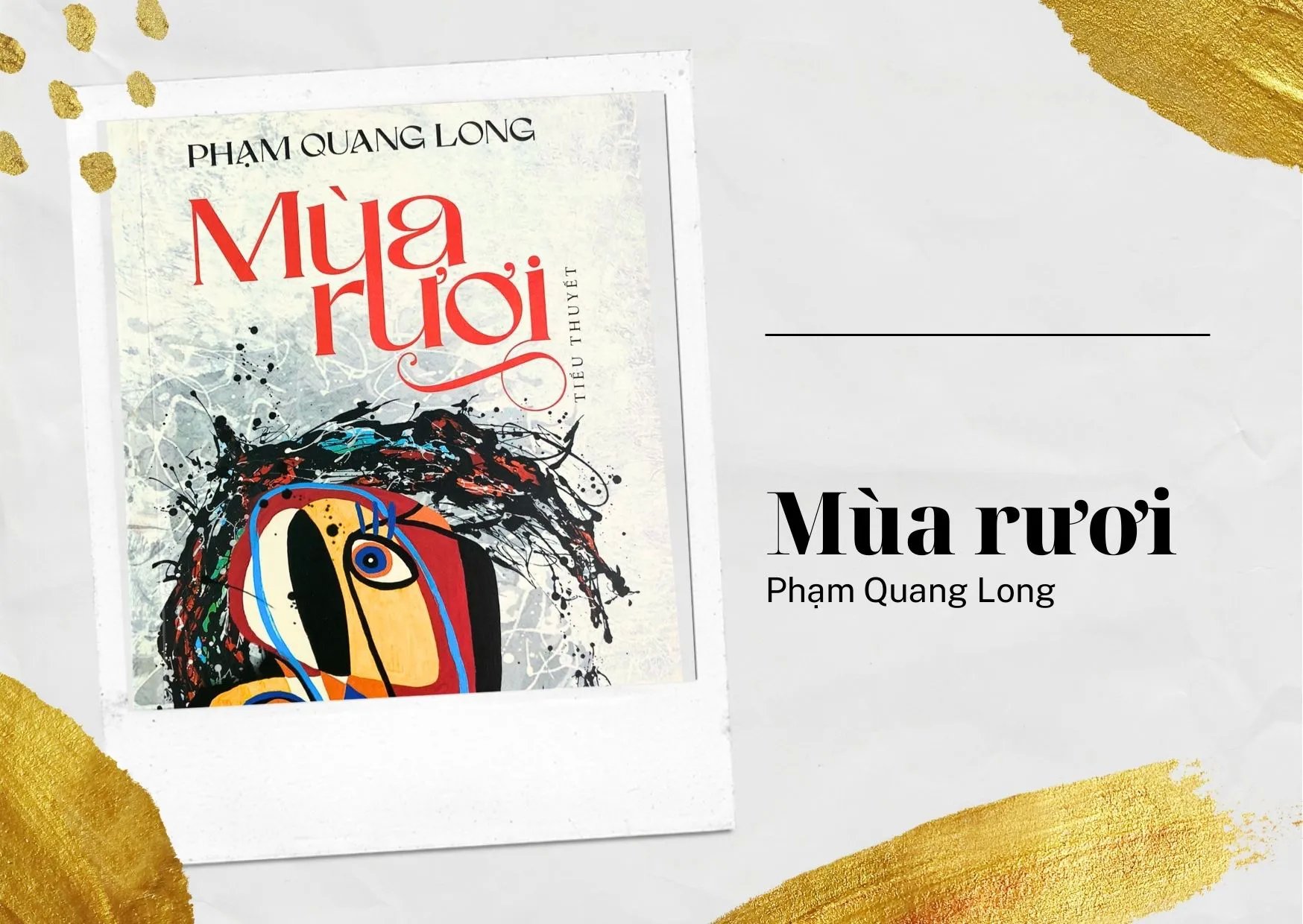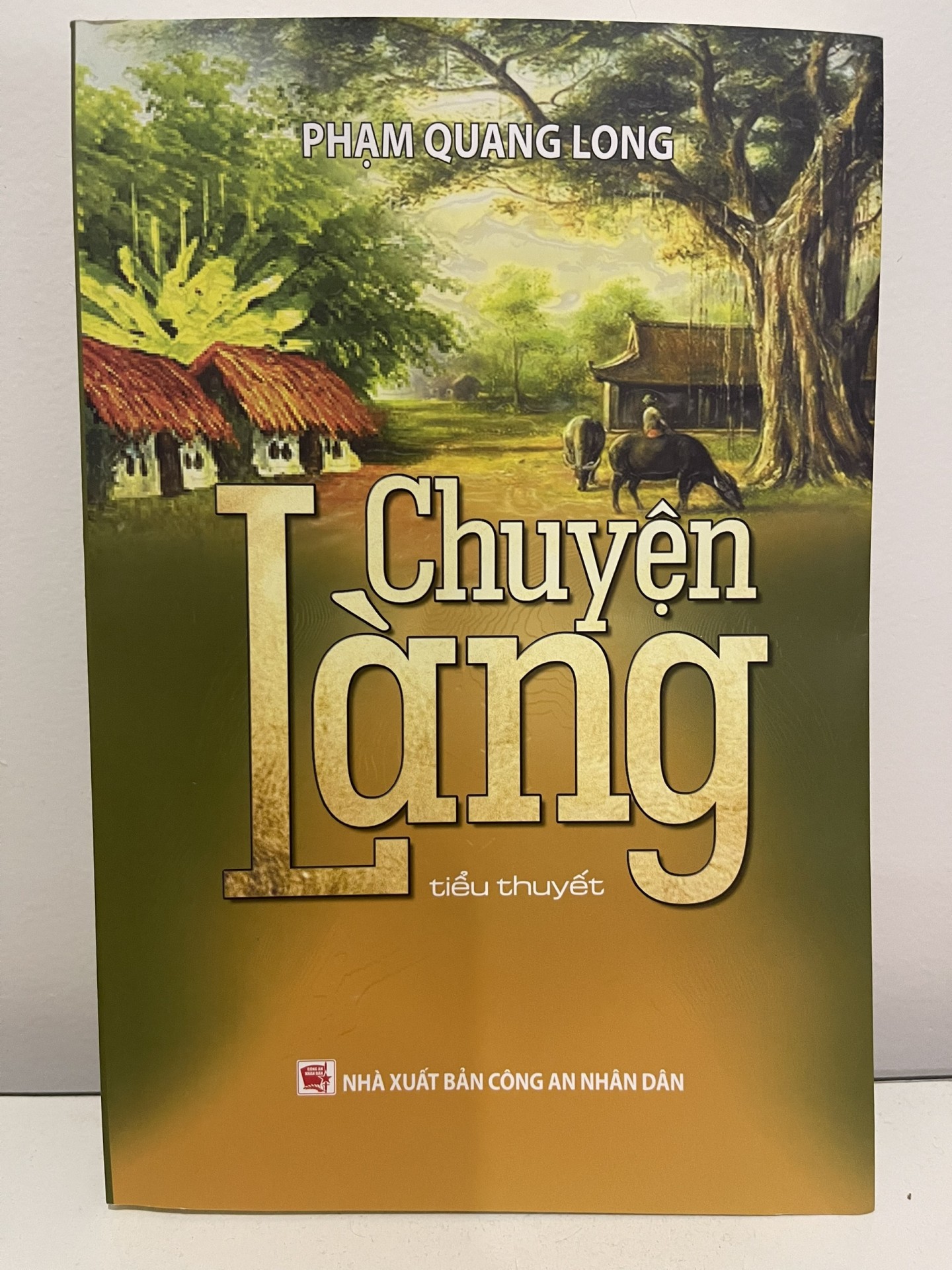在范光龙的长篇故事中,村庄的景象如同越南北部沿海平原的许多乡村地区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区。虽然这里没有风景如画的景色,却拥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河流、湖泊和稻田和谐共存,虾、鱼、螺和其他海鲜资源丰富……此外,一年四季还有许多时令农产品可供选择。然而,如同其他所有农村地区一样,《乡村故事》中的东华村和《河蟹的季节》中的华东村也经历了国家和祖国历史的起伏跌宕:战斗、建设、祈求独立、自由、衣食……这些村庄是越南农村生活的缩影,反映了构成越南民族英勇而又悲壮历史的重大事件:抗法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之路、抗美战争、新农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等等。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农民都被视为革命的强大力量,但他们的选择却最少。范光龙关于土地改革不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村集体与个人“谁胜谁负”的斗争,以及当前新农村发展政策的不足之处的论述,都真实而深刻。但最令人动容、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莫过于那些奔赴战场、献出生命的农家子弟,他们留下的无尽悲痛。这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如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深渊,深深刺痛着母亲、妻子和姐妹们的心灵,在她们的脸上留下深深的伤痛和悔恨……在那些漫长而痛苦的思念日子里,她们生活在无尽的焦虑和忐忑不安之中:“那封信在两位母亲之间传递了无数次;有时,当她们无事可做时,她们会坐下来一起读翠的信,彼此回忆,互相安慰,好让孩子们不再那么担心”(《乡村故事》——第395页);当她们在战场上与心爱的孩子们失去联系时,她们陷入了疯狂、迷茫和绝望……(《乡村故事》——第460页)。这真是一笔后世至今仍无法偿还的债务。战后时期,农民们不得不“强忍泪水”,艰难地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常常汗流浃背、泪流满面。农村经济问题有时看似“无法克服”,因为农民自身缺乏经验;他们的奉献精神无法弥补他们的潜力不足,他们的意志力也无法弥补他们的知识匮乏。农民们感到无能为力,被迫向体制屈服。诸多矛盾并存。许多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印记的农村道德价值观逐渐消逝,令人扼腕叹息,怨恨不已。范光龙在回答区领导提问时,借用了村长——一位“真正的”农民——的话,不仅表达了农民的心声,也传递了一位深爱故土的作家的情感和感悟:“……国家仍然欠农民太多。一切都依赖于农民,但农民受苦最多,他们的孩子最弱势,农村地区最不受重视,农民生产的商品养活了整个社会,但社会却根本不重视农民。卖给农民的商品价格昂贵,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商品却很便宜,农民的土地被随意征用,任何人都可以下令收回土地,而补偿却少得可怜。至于政策?好处多,弊端也多。如果一切都对,农村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就拿我们村来说,经过几十年按照你们指示的改造,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村子了。村名都没了……”“至于其他方面,对金钱的过度重视毁掉了太多东西。”最糟糕的是现在邻里之间缺乏情谊,先生……整个社会都重视金钱、头衔和利润,而您却告诉我的村民不要像他们那样生活?如果现代化毁了人,那我根本不想要现代化。”(《小龙虾的季节》——第3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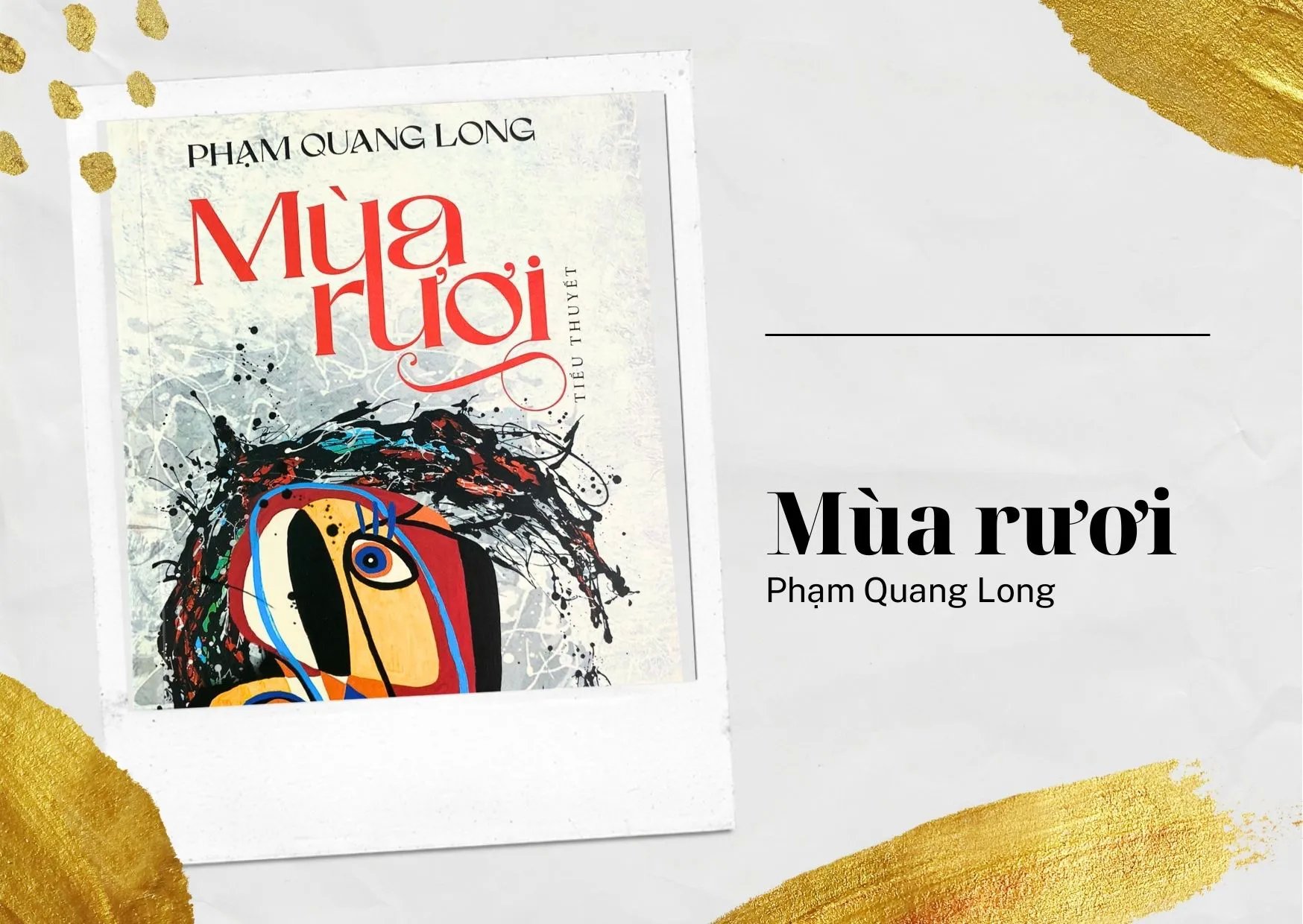
该体裁的一大潜力,将在作品中以虚构的方式清晰展现,即强调人物身份的刻画风格。这可以被视为“小说的精髓”,也是范光龙诗意风格鲜明的体现。据作者所述,《乡村故事》和《河蟹的季节》都以他出生的那个熟悉的村庄为背景,那里弥漫着乡村的宁静、质朴和温暖。尽管他已“融入”城市社会近半个世纪,范光龙始终保持着从未离开故乡的村民身份。他对村庄的景色记忆犹新:池塘、稻田、寺庙;他对农民的生活方式、礼仪和性情了如指掌。渗透到他生命中每一个细胞的经历,以及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为范光龙创作出既熟悉又真实、充满活力的乡村生活(人物和风景)画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范光龙的每一本书都描绘了形形色色、不同世代的农民:老少咸宜;贫富贵贱;善恶不一;从官员到平民百姓;从保留着农民基因的人到忘恩负义、心灰意冷、背弃故土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难以置身于时代之外;换句话说,他们总是被卷入现实的漩涡:从炮火纷飞到战后重建;从饥寒交迫到衣食无忧;从茅草屋泥墙房到瓦顶砖院,再到高楼大厦花园别墅……作为一位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作家,范光龙常常以新旧交融、过去与现在的“二元”视角审视乡村生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社会变迁之后,人们所获得的和失去的。当今乡村的面貌反映/重塑为一种多极化的存在,由多维、多方面的思维、感知和感官生活体验所塑造。
范光龙的乡村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形象。更引人入胜的是,书中大多数性格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原型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例如,古怪的老农释;聪明好学、英勇无畏的士兵翠(《乡村故事》);花东村的“毒舌大师”老环;以及在土地整治和乡村城镇化进程中,英勇善战、勤劳肯干、是村民可靠支柱的老村长丁。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正是凭借家乡著名的泥蛆特产发家致富的人(《泥蛆季节》)。这些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喜怒哀乐,塑造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和气质。每篇故事的叙事发展都表明,范光龙始终以开放、温暖、平等和民主的视角看待农民,以公平的方式与笔下的人物进行平等对话。即使是那些被视为“负面”角色、村民眼中的“眼中钉”,甚至是令他们的妻儿时刻提心吊胆的人物,即便作者似乎能“读懂”像老释和老欢这样狡猾自以为是的人的心思,最终也并未激起读者的敌意,反而传递出一种宽容和是非观。在乡村风光中,范光龙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交织着悲剧与喜剧、高尚与卑劣、善与恶……他将所有的爱、同情和共享的快乐都倾注在每个人的命运和人生故事中,与人民一同承受着最深切的痛苦:“一个小得像鼻孔一样的村子,只有四十户人家,却有近二十名烈士和伤兵?我估计每户人家贡献了一两个人。如果算上整个国家,那就更多了。真是一座白骨堆成的山,一条血流成河……”(《乡村故事》中人物的话——第464页)。在经历了岁月的变迁和贫困农村地区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之后,范光龙提炼出一种蕴含深切慈悲的处世哲学:“人生就是如此。村庄也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有一件事,必有另一件事。一百个人,一百种不同的命运……每个人都活着是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每个人要么是自己的来世,要么是别人的来世,或许是别人的前世……所以,活着的时候,就按正义行事,两方面都和睦相处,既让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长辈们说得简洁而睿智:互相观察,彼此相待。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约定俗成,但却能使人正直善良。”(《瑞时》——第227页)这是一种“妥协”,一种旨在保留人际关系之美、传递道德观念以及塑造越南世代价值观的习俗和传统的延续与适应。因此,范光龙的小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学”。它们既具备小说的特质——小说这一体裁以个人生活和人类境况为中心——又传递着同情和人文主义的信息。
在书写乡村生活和乡民生活时,范光龙尤其注重探寻和解读滋养他从童年到成年灵魂与情感的土地上的文化印记。尽管他游历甚广,并在高等教育领域担任过诸多要职——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校长、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以及一度担任文化部门“领军人物”的河内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但他的思想始终深深扎根于故土。他以文化管理者和文化接受者的双重视角来书写他的故乡。华东村和东华村都是纯粹的越南文化空间,从自然景观到生活方式、习俗和美食,无不体现着越南的独特风情。虽然这里没有高原地区高耸入云、河流纵横的壮丽景色,却拥有宁静祥和的氛围:成排的树木、河畔码头、寺庙、村舍、池塘和农田……农民既是田野的耕耘者,也是这片土地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这片乡村的独特风貌历经岁月洗礼得以保存和传承,真正从最“古老”、最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汲取养分,蓬勃发展。孩子们玩弹珠、放风筝、游泳等游戏,以及当地居民亲手加工的鱼、虾、螺、虫等丰富的自然物产,都被范光龙珍藏为记忆的宝藏,并成为他灵魂深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当代热爱描写美食的散文作家中,范光龙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佳作。从简朴的乡村菜肴,到对每一个细节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的描述,他将风水哲学和个人见解融入每一道菜肴之中。可以说,他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专业厨师,呈现一份长长的“菜单”,其中每一道菜都美味可口,令人垂涎欲滴,刺激着读者的味蕾。每道菜的香气和味道似乎都渗透到字里行间,引人入胜,令人动容:“刚煮完一锅红烧鲈鱼,锅底铺着姜叶,裹上稻草,再盖上燃烧的稻壳……鲈鱼个头很大,肉质肥厚精瘦,用鱼露和盐调味恰到好处,配上几根一起炖的熟透的香蕉,佐以刚煮好的米饭,真是美味无比”(《乡村故事》——第51页)。虾和泥蟹,这些咸淡水交汇地区的特产,在一位经验丰富的美食家的细致描写下,栩栩如生:“这里的虾比普通虾大,每只都像拇指那么大,炖煮后肉质紧实鲜甜,令人回味无穷。但最美味的还是泥蟹,每只都像鲤鱼那么大,雌蟹满是蟹黄,雄蟹肉质紧实如米团,肉质丰富……将泥蟹拔出蟹钳,蟹腿分别捶打,挤出汁液,剥去蟹壳,取出蟹黄,将汁液加入锅中慢炖,撒上少许切碎的槟榔叶增添香气,蟹黄像星星一样漂浮在金黄色的蟹黄旁边,宛如姜黄。配上刚煮好的米饭,锅里和电饭煲里的饭菜都会被一扫而空。这道菜不仅美味,更让人联想起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习俗和这里的思维方式,仿佛在诉说着许多故事。”(《泥蟹》)季节 – 第 103 页)。菜单上琳琅满目的菜肴充分体现了乡村风情,其中烟熏蜗牛和红烧河蛆尤为引人注目,它们独具特色,烹饪方法也毫不逊色于其他美食:“挑选十只成熟的蜗牛,它们口中充满内脏,壳顶向外张开,壳下泛着一层朦胧的蜡质光泽。将蜗牛放入一个大篮子里,盖上筛子让烟灰漏下去,然后放在阁楼里,离烹饪区稍远一些,以免过热。几个月到半年后,就可以取出食用。这些蜗牛通常生活在池塘里,需要水,但放在阁楼里只吃烟灰,却能存活下来,变得肥美洁白,这真是令人惊奇。每只蜗牛都肉乎乎的,肥美多汁,黑色部分呈深褐色,白色部分呈乳白色,全是油脂,看起来非常诱人,而且完全没有黏液和污垢……蜗牛被切开……”底部,用鲜活的食材烹制而非水煮,并用……腌制。“将适量的南姜和姜黄与少许五花肉和烤豆腐一起翻炒。煮至刚熟的香蕉与炒好的蜗牛一起炖煮,加入一碗清醋,直至液体蒸发,只剩小火慢炖。加入葱、槟榔叶和空心菜,待香草略微蔫软后即可食用。盛于碗中,边吹气边吃,使其凉快,然后大口吸溜——这才是极致的享受。”(《乡村故事》——第345页)越南北部著名的海虫菜肴,曾因武邦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精彩文章而备受赞誉和着迷,如今又被范光龙誉为“终极美味”,因为它的食材新鲜、纯净、营养丰富,而不是那些装饰精美、赏心悦目的著名海虫饼。但要做出真正高品质的菜肴,需要一丝不苟的努力和技巧,其精湛程度不亚于一位大厨:“炖蠹虫一定要用陶锅烹制;铝锅或铸铁锅都不行。首先,要准备大量的姜,在锅底铺上两层左右。但铺在锅底和锅壁上的姜叶要巧妙地铺成几层,这样调味料和蠹虫粉才不会散落到锅底,破坏菜肴的鲜美,也让蠹虫变得干柴。因此,姜叶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粘锅,但姜叶在烹煮过程中会释放出浓郁的香气,随着蠹虫逐渐变软,香气也渗入其中。食用时,你会同时感受到姜的香气和淡淡的辛辣味,非常宜人。那微妙、细腻、令人着迷的辛辣香气”(《蠹虫季节》——第122页)等等……如此冗长的描述,也是一种享受美食的方式。品尝菜肴的滋味,并充分领略作者倾注的心血、热情和远见。因为,在美食的故事背后,蕴藏着构成越南北部三角洲文化认同的各种元素的象征和融合。这种烹饪艺术与稻作文明的根基和特征相伴数千年,如同越南文化绚丽多彩的马赛克中一块简洁而鲜活的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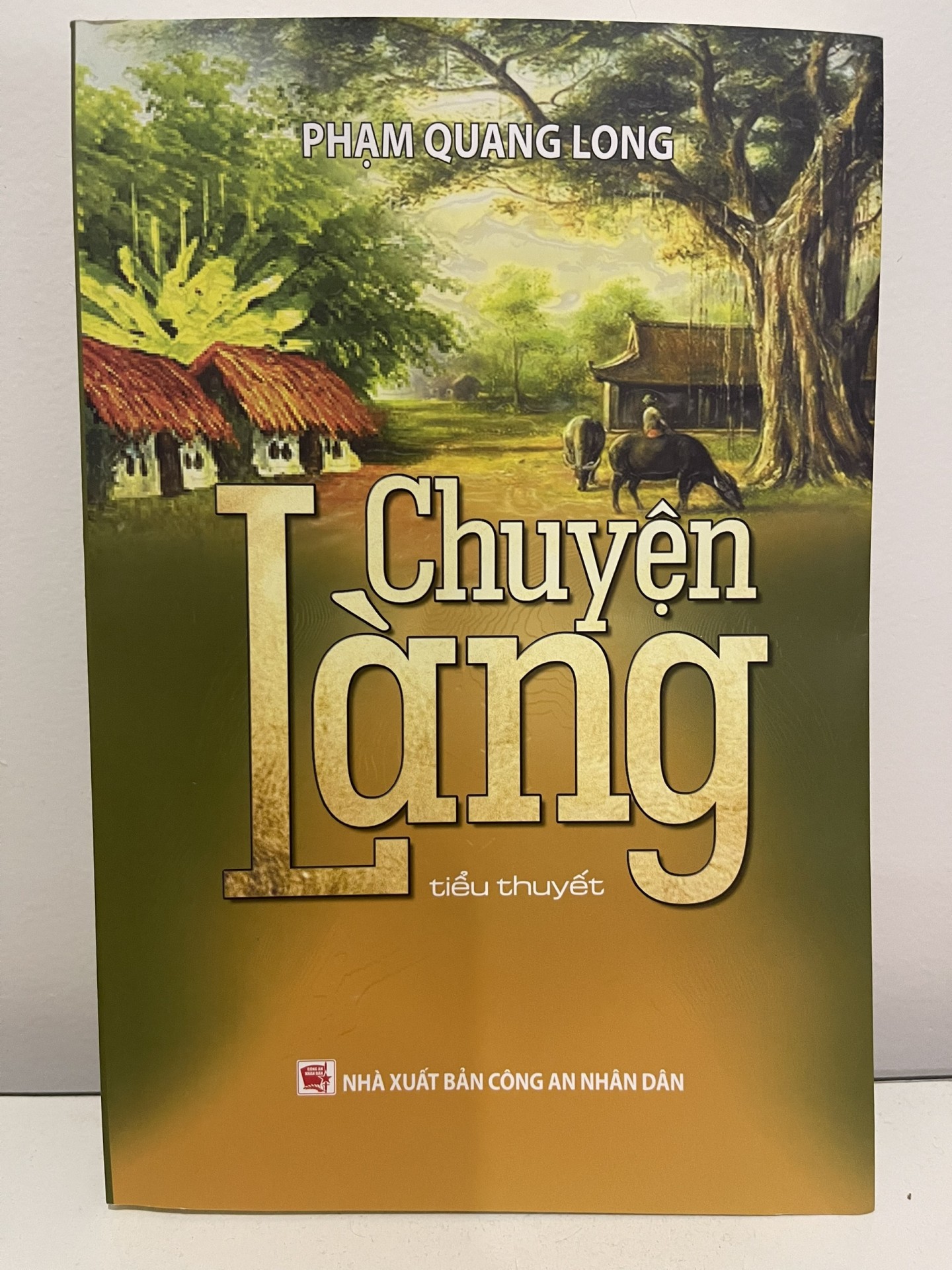
除了保护和传播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之外,范光龙的小说还描绘了乡村生活的另一个极端现象:在广袤的沿海地区,构成越南价值体系的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正在逐渐消逝和衰落。这深深触动了他的文化敏感度。当代乡村生活的现状引发了他诸多反思、焦虑,甚至难以置信和困惑,因为他目睹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坚韧不拔、能够抵御任何违背悠久习俗和传统的事物的村庄里,竟然出现了粗野野蛮的行为。曾几何时,人们以根除迷信为名拆毁寺庙,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对精神生活和传统信仰的不敬,而这些精神生活和传统信仰在越南历史上一直是人们的救赎和庇护:“人们有祖先,也有自己的信仰。先生,当你不再相信任何事物时,灾难就开始了。我并非妄言。祭祀祖先和神灵以求庇佑和祝福是人类的传统,怎能称之为迷信?慈悲的佛陀一直教导人们要行善积德,切勿伤害任何人。”(《乡村故事》——第80页)混凝土建筑肆意妄为的趋势不仅造成了生态破坏,扰乱了自然景观,也严重损害了道德和社区精神:“村子的面貌越来越怪异。崎岖不平,摇摇欲坠。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房子,无暇顾及他人的房屋和事务……人们的心灵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纯朴。私利正在改变村子的面貌,也改变着村民的面貌。完好的地方越来越少,破败扭曲的地方越来越明显……人们只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却不关心过更体面的生活”(《小龙虾的季节》——第336页)。就连乡村里清澈悦耳、令人心旷神怡的风笛声,也因为人们“放弃”了这“傻瓜”般的轻柔合唱,而变成了污染源。宁静祥和的氛围被“嘈杂”的声音所打破,“如同重拳出击,充满挑衅”,“偶尔还像狗一样哼哼唧唧”……在这些暴露出来的反文化悖论背后,是对在改革开放时代,在市场经济、一体化和交流的背景下,旨在保护和弘扬越南价值观的文化协议的关注和反思。
在叙事艺术和诗歌特色方面,范光龙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写作风格与创新探索。他两部作品中时空意象的运用,虽遵循线性叙事,却并不僵硬单调,而是灵活多变。其叙事结构中,时间顺序与平行时间、怀旧时间、回溯时间交织融合……现实空间与精神空间并存,自然空间与社会语境交相辉映……此外,他精湛的心理描写技巧也是范光龙作品的一大亮点。他摒弃了迷宫般结构和漫无目的的意识流写作手法,避免了令人费解的晦涩难懂,而是以深刻的心理剖析和描写,展现出对人性与世事的深刻理解,深深吸引着读者。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主角)都拥有丰富饱满的内心世界,经历着复杂而多面的发展。最后,文本结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各种情绪和语调的融合与交织,营造出一种复调式的质感:庄严与幽默、同情与嘲讽、妥协与辩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物的对话中(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范光龙毫不犹豫地让他们自由使用粗俗的语言,但这些话语并不令人感到淫秽或冒犯。相反,它们如同调味剂,为文字增添风味,带来纯真而清爽的笑声,缓解人们的沮丧;就像一种有效的减压良方,帮助人们在感到疲惫和压力过大时放松身心。文化研究员阮清(曾任太平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厅长)分享了他对这位志同道合的同胞的深切情感:“在范光龙先生的大部分小说中,他都试图传达他对世事的忧虑和焦虑,同时也借此机会颂扬善良与美好,并寄希望于人际关系和世事能够复兴,回归高尚与美德,正如他自幼年起所受的教导和体验”(《河蟹之季》——第9页)。贯穿范光龙作品的是他对家乡勤劳人民的热爱,对他而言,写作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行为,一种偿还他对祖国、对国家的责任的行动……
然而,尽管范光龙拥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仍需更加精挑细选、克制笔法,舍弃过于繁复的细节,使情节更加简洁明了。此外,他有时过于喜欢辩论和论证,令读者感到疲惫和头疼……但这些不可避免的不足并不妨碍这位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作家作品的传播和蓬勃发展。
从一个“小如牛蹄”的村庄意象/原型出发,通过无数关于土地兴衰、人生苦乐、以及对人性之善与高尚德行的信仰的故事,范光龙重构了一个既熟悉又独特的现实整体。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始终蕴含着深刻的人文主义灵感,并开启了关于民族文化话语的复杂对话。
(*)《乡村故事》——人民警察出版社,河内,2020年
(**)泥虫的季节——文学出版社——河内,2022年河内,2023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