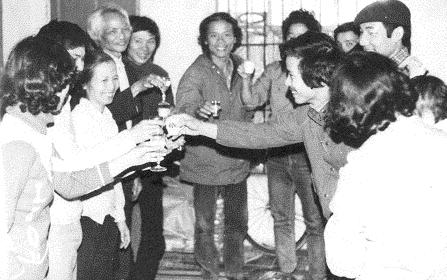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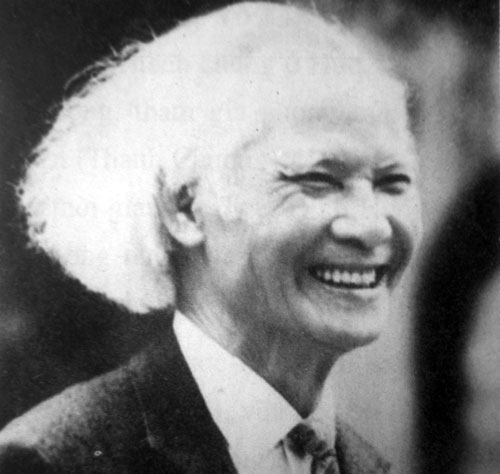
副教授兼功勋教师陈廷虎(1926-1995)
1. 我在足球场上拼命奔跑,这时陈玉旺教授向我招手。“薇,明天早上跟我去嘉林。我好着急。胡先生家漏水,所有的书都湿透了。那些都是很珍贵的书。我借了俊(诗人杜明俊)的自行车。我们能到吗?”
那是1974年的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离开美池宿舍。我们骑着摇摇晃晃的自行车,沿着雾气弥漫的道路,穿过龙边桥。我们轮流蹬着车。红河左岸在低垂的阴云下蜿蜒流淌。家乡的天空很少如此阴沉。经过周贵后,我们来到一栋破败不堪的茅草屋前,它依偎在另一户人家的花园旁。这房子和我1966年美军轰炸期间居住的那间三居室小屋非常相似。我的老师们的生活与无数次的疏散交织在一起。老师们拉起窗帘迎接我们。一排书架,有的用竹子做成,有的用粗糙的木板做成,都摇摇欲坠地靠在地上,上面盖着席子和麻袋。几本俄文书籍精致的书脊从里面探了出来。我抬头一看,房子不仅仅是漏水。椽子和竹条都断了,被推到了一边。茅草屋顶已经碎成了好几块。我透过窗户问道:“那是谁的竹丛?我们能拿几根吗?”“好啊!我们都是亲戚。”“村里有稻草吗?你能帮我去要几捆吗?”“可是怎么弄呢?”“我们不能再饿死了,先生。我们重新盖屋顶吧。我可以的。”老师有些怀疑,让她去要稻草。我拿起刀,冲到竹林里,砍了三根竹子,带回院子里。两根老竹子已经劈成了椽子,还有一根是细嫩的嫩竹子。然后,我爬上屋顶,把所有旧稻草都扔了下来,让王先生把它们收集起来,留着以后再用。原来北方人盖房子很随意,不像我们这种经常遭受风暴侵袭的乡下人那么用心。屋顶很快就焕然一新了。低头一看,只见老师来回踱步,一脸担忧。王先生负责一间房,我负责另一间,迅速地把竹条捆成一排排。“瓦房结实,茅屋是用竹条搭的,”捆好后,屋顶很稳固,我们可以放心地在屋顶上走动。稻草也是刚弄到的。我用稻草一块一块地盖屋顶,优先用新鲜的稻草盖外面的房间,那里放着床和书架。到了中午,后面的屋顶已经盖到了山墙。我们爬下屋顶吃饭。阳光从屋顶照进碗碟里。这是一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饭菜。味道从未如此美味。她炖了土豆、猪蹄、鲜红的西红柿,我想里面甚至还有芹菜。她特意给了我一大块厚厚的方形猪蹄,足有茶杯那么大。我狠狠地咬了一口,猪蹄就从牙缝里滑了过去。哦,我的天!我这辈子第一次尝到了如此美味的东西。我至今仍记得那件事。老师笑着说:“别担心,刚才看到你爬上去把屋顶踢下来,我可担心死了,以为要花好长时间,都准备叫人来帮忙了。前面的屋顶怎么办?” “老师,别担心,”我一边说着,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第六碗米饭。碗已经满了,下午肯定更快。我小心翼翼地把屋顶加固好。毕竟,这房子屋顶漏水。到了日落时分,一切都搞定了。一壶热腾腾的茉莉花茶,两兩(越南货币),让人感到无比舒心。这时,老师坐下来,愉快地聊着天:
你们真有才华。我什么都不会。小时候,村里把我送到顺化读书,希望“一人成官,家道中落”。我只会读书,对绘画、竹编一窍不通。我给你们讲个儒家老学究的故事。我的老师和阮泰根教授的老师是好朋友。他们来访时,我得给他们倒茶。屋顶漏水,他们就把漏水的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又漏了,他们又挪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漏水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找,没完没了。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一天之内把漏水的地方补好呢?儒家学究就是这样,你们知道的。孔子四处讲学时,看到路边田里有个农民正熟练有力地用桶舀水。他的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孔子写道:“智慧源于心智。”看来儒家不太喜欢实用科学。哈哈……
我们连夜步行和骑自行车离开,以便第二天早上能去上学。

副教授、优秀教师陈廷虎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2. 1975年底,我接到裴维坦教授布置的关于阮廌的论文作业。一天下午,我在一排龙眼树下的石桌上打乒乓球,裴维坦教授突然从前面那栋楼三楼的阁楼探出头来,喊道:“喂!喂!你这小矮子!上来!”我扔下球拍就上了楼。他训斥我说:“你这是要吃乒乓球吗?还是看书吧!明天我们要去国家图书馆。这是你的介绍信。去特藏室申请查阅。”他摸索着掏出两枚越南盾:“这是电车票!你们这些城里人,别想不付钱就溜进去!”我只能颤抖着接过钱。那时,教授的工资最多只有75越南盾,而且家境贫寒。我在河内的兄弟姐妹一个月最多只能给他 5 越南盾,但这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我过去常常坐在图书馆里,有时要花一个多小时坐电车才能到。有些时候,为了请朋友吃糖,我会偷偷溜上火车,或者一口气走上十公里。幸运的是,在1965年的油印版《哲学公报》上,刊登了陈廷虎教授的一篇题为《阮廌》的文章。这篇文章犹如一道巨大的开端,帮助我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在引言中,教授写道:我们目前对阮廌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孤立的岛屿,以及海平面上升后隆起的山峰。同时,想要全面研究它的地貌特征实属不易。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跨学科、全面且客观的研究方法。
我知道科学研究非常严肃艰辛,不像写诗或闲聊那样轻松。历史总是经历诸多变迁才呈现在我们面前:战争、否定,尤其是偏见。阅读“真实的历史”非常困难。在讲座和研讨会上,我尽力记笔记、记录信息,并就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提问。教授家离我家太远,所以我没能去拜访他。
1976年,我继续撰写关于阮廌的三年级论文。那时,我的导师已经搬到了禄德,住在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去向他请教未来的研究方向。我的导师仍然是裴维坦教授。那时,我和胡教授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知道他是我高中老师邓铮先生的好友,邓铮先生待我如亲生儿子一般。胡教授吐出一口烟斗里的烟,突然问道:“薇,我问你,你觉得哲学有趣吗?你对哲学有什么看法?”我如实回答:“我觉得读哲学就像读小说一样,我全都懂!”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叠薄薄的手写稿,说道:“读读这个。我去街上买包烟。”
我快速读完了。那是康拉德《西方与东方》的一个译章节。我刚读完,教授就到了。他坐下,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接着解释了他写的内容、他的观点,以及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教授似乎很高兴,说:“这说明你理解得很透彻。说实话,我教书,但我并不认为学生能完全理解我讲的内容。啊,看来学生们确实理解了!你们班有多少人读书?”“图书馆每周给每个学生借12本书。很多学生都很有热情。”“那可真不少!太好了!疏散期间我们没借到这么多书,几乎没怎么读书。”教授拿起那份文件,轻轻掂了掂,好像在称重,然后突然递给你:“这是给你的。我这里有一份打印稿。系里的资料也都有。你带回家仔细读读。”
我一直珍藏着这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它陪伴我度过了战后饥荒、多次搬家,以及房屋的建造和翻修。老师的字迹纤细而斑驳,仿佛还能看到当年他汗水浸透的痕迹。他翻译的每一个字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977年全年,在裴维坦教授的指导下,我继续研究阮廌,以完成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我更频繁地拜访了胡教授和潘大端教授。一位教授研究思想,另一位教授研究历史,他们都来自“我们的家乡”。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前往上信、昆山、林山、林城、武光……有时像真正的乞丐一样乞讨食物,饥寒交迫地跋涉。
稿子完成后,除了交给陈玉旺先生阅读并修改他所谓的“愚蠢”之处外,我还把书带到了老师家。他当着我的面认真地读了一遍,立刻说道:“真奇怪!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有人称阮廌为‘文化人物’。你怎么敢这么写?算了!”我回答说:“谭老师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人们称阮廌先生为各种‘阶段’,但就是不称他为‘文化人物’。你再想想……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关系很亲近,我便大胆地继续阐述我的观点。最后,我说:“阮廌也是一位农民,一位博学的老农民,一位老师。”我摘录了几句阮廌的诗句并评论道:一餐两用,众人所求 / 两股线,三股线,贪婪者的诅咒“住在乡下是什么感觉?”田野是主人,人是客人。“农业实践经验怎么样?教授就坐在那儿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谁告诉你的?’”(后来,我向黄玉贤教授汇报工作时,发现他们俩很像,都不停地说“哦,真的,真的,真的”)。幸运的是,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阮廌列为世界文化人物。
到了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教授高度赞扬了我勇于坚持自己观点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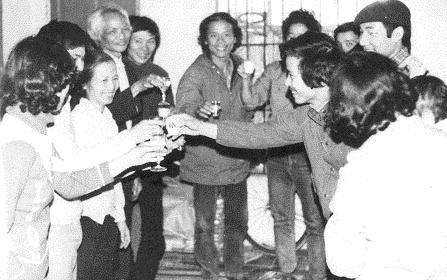
学生们纷纷表示祝贺。副教授、优秀教师陈廷虎(从左数第四个)
3. 1978年,我留在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但研究方向从中世纪文学转到了民俗学。我再次向我的教授请教。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指导:
首先,你应该先研究泰族。研究占族比较复杂,研究高棉族又太牵强,而杜志先生已经很好地研究了芒族;你最好不要去碰黑猩猩。泰族非常重要;京族人口只有三分之二是泰族人,而且他们的领土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曾经从缅甸一直延伸到台湾。他们也是我们京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来源。这不是开玩笑;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我再说一遍,这非常重要。我会介绍邓严文先生给你认识;他在中央少数民族学校任教,所以他掌握很多信息。
其次,你不应该学习我的写作方式。我的写作基于经验积累和对想法的提炼。我不是像黄宣汉先生那样的研究员或“会计师”。如果你照搬我的风格,你的经验从何而来?你很容易陷入臆测。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叫做“妄下断言”。向坎先生学习吧;他非常严谨,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资料研究,一旦完成,文章就完成了。严谨的研究本身就具有说服力。这才是你应该传授的。精简你的论点;不成熟的论点是一把双刃剑。
我无法听从泰老师的建议,因为我无法忍受几次山区实地考察中的饥渴。战后贫困是沉重的负担,人们甚至连衣服都穿不上。我做了些调查,但老师讲的内容我只听懂了一半。
1980年,老师听说我打算回老家结婚,就把我叫去谈话。这一次,老师的语气像是一位父亲:“我听说了这件事,接下来我要说的两件事,是绝对错误且不可接受的。”
首先,你打算娶她只是为了照顾你年迈的父母,对吧?这太不人道了。女人不是你的奴隶,她们已经够苦了。娶一个女人只是为了让她“下地干活养老”,这种做法太自私了,只会加重她们的痛苦。你一年能回家几次?她们要独自睡多久?你不能把她带过来。
第二,在我们这一代,夫妻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分居。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结果一事无成。别重蹈覆辙。安定下来是成功的第一步。你应该娶一个本地人,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互相扶持。你会很快老去的。
我静静地坐着,心想,幸好那只是个想法。他53岁时跟我说过这句话:“你会老得很快。”今年我已经60岁了。老师,无论我写了什么,我再也没有机会与您分享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孤儿,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我非常想念您。
河内,2015年1月29日。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阮雄维
最新消息
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