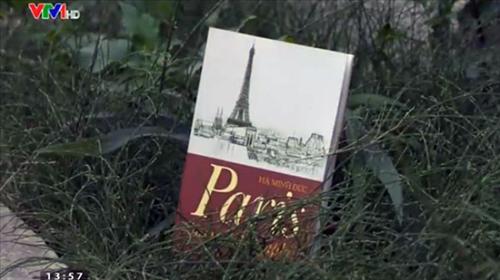
作为他的学生,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这位杰出的人物已经习惯于一项工作——在“文字的领域”耕耘,以至于无法挣脱。写作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和肌肉,如今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玩转”文字。或许对于从事同样工作的人来说,晚年写作可能只是一种轻松的消遣,但河明德依然坚守在“文字的领域”。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正因如此,即使退休之后,人民教师河明德仍然默默地、秘密地继续出版新书。巴黎“两个秋天再次相遇”这是一本这样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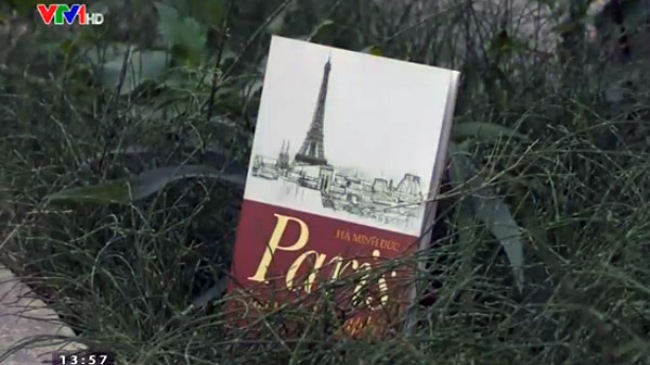
哈明德教授所著的《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一书
“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实际上,这是哈明德教授两次巴黎之行的文章合集,两次行程相隔近20年:一次是1994年访问里尔新闻学院,另一次是2014年8月重返巴黎。至于是什么意想不到的巧合促成了这一切,目前尚不清楚……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或者更确切地说巴黎 (二十个秋天之后,我们再次相遇)由 Ha Minh Duc 教授撰写二十年后19世纪法国作家亚历山大·仲马(老仲马)的诗句《二十年后》(Vingt ans après)恰巧也与数字20有关(“二十岁,当人生方向明了/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踏上旅程”——裴明国)。仲马是著名小说《二十岁后》的作者。三个火枪手我被四位年轻人(阿尔达涅特、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为追求正义而展开的冒险故事深深吸引,他们秉持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信念。即使二十年后,他们不再年轻,依然带着最初的热情重返战场(在另一本书中)。我在书中读到……巴黎“两个秋天再次相遇”何明德教授也同样充满热情,但他的热情在于求知。这位“人民教师”一生似乎都全身心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对他而言,这些旅行绝非纯粹为了休闲。当年轻人在难得的闲暇时光里尽情享受生活乐趣时,何明德却来到了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巴黎,一心扑在研究和记录与他的职业相关的资料上。而他的职业并非仅仅是教授和研究文学。他也是一名记者,甚至是一位“真正的”记者,因为除了亲自撰写数百篇新闻文章和书籍外,他还是河内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如今,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已被年轻的教员们发展壮大,成为越南最强大的新闻与传播培训中心之一)。或许正因如此,当他第一次踏上法国的土地时,他感受到了如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初次到访异国他乡般的兴奋。记者何明德真诚地表达了这种感受:“我受越南记者协会委派,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了法国里尔新闻学院。作为一名新闻教师,我很高兴,因为这次旅行与我的职业息息相关,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访问法国。”参观位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里尔新闻学院。。

教授、人民教师河明德
我还没来得及读完河明德教授近期出版的所有著作。这是因为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涉猎广泛,涵盖研究、文集、汇编和诗歌等多种体裁。散文一直是他数十年来最喜爱的文体。自从他出人意料地涉足一个与他长期从事的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的领域后,我注意到他变得更加沉稳,也更显年轻活力。他创作诗歌和散文时,都带着探索周遭世界的热情,如同一个初次体验人生的年轻人。他半个世纪以来磨练出的研究技能,赋予了他的散文必要的深度。而诗歌,则如同催化剂,让他的散文得以翱翔,避免了它们过于枯燥乏味。
这份期刊游走于研究与创意写作之间,而哈明德正是在这片“领域”中保持并磨练着他丰富的潜能:观察、记录和分析的习惯。的确,我意识到……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这正是这位作家的优势所在:他几乎毕生都在勤勉而真诚地追求生活中的一切新知识,以充实自己。我敢断言,河明德迄今为止创作的大量作品正是建立在这种勤勉努力的基础之上。河明德的散文写作风格朴实真诚,不矫揉造作,因为他深知写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启迪读者,激发求知欲。阅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巴黎“两个秋天再次相遇”我们总能感受到作者朴实无华、真诚坦率的叙事风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Ha Minh Duc 对现实的把握非常迅速而精准。在参观里尔新闻学院时,他写道:“人们常说,来到这座北方城市,你会哭两次,一次是相遇时,一次是离别时。”(《参观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新闻学院》)。他以记者的严谨细致,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有趣的信息:“里尔人口约1,153,113,仅次于巴黎、里昂和马赛。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42%的居民年龄在25岁以下,拥有近10万名学生、数千名研究人员、众多大学,尤其是里尔新闻学院。”关于巴黎第七大学,他也提供了相关数据:“该校拥有26,000名学生、6,000名国际学生和200个合作单位。”说实话,我本人也曾在巴黎第七大学实习,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与文学系的许多教授共事,但我从未知道过如此具体的数字。而河明德教授无论走到哪里,都渴望在他的笔记本(他总是随身携带)上记录下准确具体的数字。作为一位几乎毕生致力于研究和教学(在大学和文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当他进入新闻领域时,他那份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职业基因”似乎依然萦绕在他心头,从未离开过他。因此,记笔记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他所到之处并非像许多人那样只是旅游景点,而是经常前往研究中心、教学中心或学术活动场所。无论走到哪里,他的首要任务都是迅速收集和获取信息。在法国共产党《人道报》新闻发布会上,他与一些熟悉的法国朋友会面,这些朋友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始终全心全意地支持越南革命。他立即分享了参会人数:“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多;一些报纸报道说有60万人,但实际人数还要更多。” 在他访问的其他地方,情况也一样:里尔新闻学院、巴黎第七大学、凡尔赛宫、丽都剧院,甚至法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德国、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读者们看到的是他朴实、真诚而准确的记录——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始终保持着专注和认真的态度。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当我们说河明德的写作风格简洁真诚,笔记中充斥着数字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缺乏灵魂。事实上,河明德在做笔记时,仍然受到他作为研究人员背景的影响。他对数字和精确性的偏好是正常的。对他而言,写作中最重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华丽的辞藻”。他重视细节,并通过数字来体现准确性。对于他在旅行、工作和文化中心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河明德都习惯于以学者的视角来对待。民间故事讲述者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关于巴黎的部分……“去丽都剧院看一场舞蹈表演,顺便买些名牌商品。”他本人就是这样展现了他的回忆录写作风格的: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这些是我在短暂游览这座大城市期间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虽然这篇游记略显仓促,但作者以真挚的视角和诚恳的笔触,表达了对巴黎的真挚情感和难忘回忆。
河明德写作风格的另一个优美之处在于: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他的幽默、机智和智慧也与法国人的精神和性格有着深刻的共鸣。事实上,这正是河明德在日常生活中为人熟知的特质。我至今仍记得我们曾在河内大学(现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共事的情景;在严肃(有时甚至气氛紧张)的会议上,河明德的意见总是最受期待的。他确实拥有出色的演讲才能。他的表达清晰简洁,但最重要的是,他风趣幽默。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他都懂得如何巧妙地用温和、圆滑、略带幽默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很少有人会因为他的“玩笑”而生气。这种风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巴黎“两个秋天再次相遇”例如,在他第一次到访巴黎时,漫步在被誉为欧洲最优雅的街道上,他突然想起文化名人许玉(Huu Ngoc)对这座“宏伟”的首都巴黎的描述:“巴黎周长36公里,长12公里,宽9公里,一年下雨164天,下雪13天,有27万只狗(人行道上每隔35米就有一堆狗屎)。”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禁捧腹大笑。当然,这些只是相对数字。如今的巴黎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也更加现代化。“巴黎街头的狗屎”这个说法倒是十分贴切,因为这里养狗的人很多。狗是人类的“亲密朋友”,但它们恐怕无法像人类那样“彬彬有礼”。在法国首都的街头遇到一些不太“文明”的事物,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写道……去丽都剧院看一场舞蹈表演吧。……(一家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特别剧院,以女舞者“清新脱俗”的表演而闻名),他一进门就真诚地问检票员:“我视力不好,请让我坐近一点;坐远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番真诚的告白揭示了(据我理解)一个极具“审美情趣”的河明德。河明德一直以来都热爱美。我认为这也是他工作和生活中“如鱼得水”的动力之一。他与“美女”的合影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特点,有时是与一位来自里尔的新闻系学生,有时是与一位俄罗斯实习生,甚至是一位捷克女研究生,他经常用这些照片来配图。此外,为了丰富这本新散文集,河明德几乎在每篇文章后都附上了诗歌,作为他“亲眼所见与道听途说”的笔记(类似于19世纪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笔记风格),以“附录”的形式补充其笔记的原始真实性。或许这也是河明德散文写作风格的一个特点,而且……巴黎“两个秋天再次相遇”具体来说,为了创建一个唯一标志河明德自己的……
初春时节,悠闲地阅读回忆录。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我逐渐认识到何明德教授的另一项才能——他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老师。2015年,这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已年届八十。看来他依然妙语连珠,文思泉涌。我衷心祝愿他,在他步入“耄耋之年”(甚至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多年)之际,身体健康,继续积极投入生活,满怀热情地追求美与创造力,并充分发挥他的潜能。第100个春天所以“20年后”,将会出现更多类似“巴黎,两个秋天的重逢。。
作者:Tran Hinh
最新消息
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