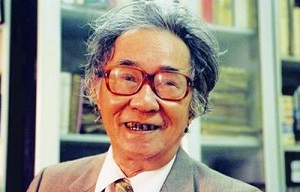
1. 享年95岁的潘玉学者,是河内师范大学早期文学院(1954年)奠基一代教师的最后一位讲师。该学院是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以及河内综合大学的前身。潘玉学者才华横溢,秉承着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密不可分的学术传统,如今安息主怀。他历经动荡时代的种种磨难,最终得以长寿,这得益于他纯洁的心灵,他一生只在书本中寻求快乐;也得益于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他留下了勤奋自学的典范,展现了克服时代困境的坚定意志,精通十几种外语,并翻译了数十部作品,涵盖文学、科学等众多领域,语言也十分多样,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文言文、拉丁语、希腊语等等。面对如此宏伟的知识丰碑,我们难以一蹴而就地领略其全部精髓,因为这座浩瀚的知识宝库已被无数国内外学者反复思考、探讨,甚至奉为真理,从灵光乍现的思想到严密的论证体系,无不囊括其中。鉴于我知识的局限,我选择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我希望记录潘玉在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贡献(或许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些领域他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时候,我常陪爷爷去拜访潘玉先生,但那时他人生中的“往事”早已如流水般消逝。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震撼。那天,他已过了“高龄”,但他那坚毅而温和的气质,沉稳而庄重的风度……正如我心中来自遥远云雾缭绕的东方圣贤。从那最初的印象开始,我便更加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从他在“文化故乡”顺化的童年,到在越北艰苦奋斗的岁月;从他与汉学大师饶宗义的对话,到在著名的巴黎索邦大学的会议室里侃侃而谈……等等,我常常拜访他和他的妻子,认真聆听他讲述自己无比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是他的本名,如成(Nhữ Thành),后来他用这个名字作为笔名,这个名字最初是他父亲从宋代儒家不朽名作《西明》的倒数第二句中取的:穷人在荒野中更喜欢使用玉石。(张泰)进一步解释说,他的名字来源于他出生地的一座山(清化省静嘉县玉山);他曾向胡志明主席求助,希望能够及时返回家乡,将父亲从极左时代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还谈到了《文学的任务不是阐释政策》这篇文章及其后续影响等等。但每一次谈话,无论长短,无论匆忙还是悠闲,最终都会回到他永无止境的职业思考上。我明白,对他而言,人生的价值体系在哪里。我记得他的作品:
2. 一百多年来,《金银花传》一直是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因此,对它的讨论、评论和研究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众多关于《金银花传》的著作中,探究阮攸《金云翘传》的风格(该书基本完成于1965年,后经多次修订,最终于1985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式著作。即使是严谨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这部著作为学术界赢得了声誉”,而一些(略显极端的)结论则认为:“潘玉对《金云翘传》的研究最为卓越。” 通常,对《金云翘传》的研究仅关注文本本身,分析其语言之美和情节的人文精神,然后根据作者的个人理解,对其进行赞扬或批判。因此,围绕金云翘的命运,引发了诸多文学争论。潘玉站在这些争论的核心,阐明了他对《金云翘传》的独特而引人入胜的解读。
首先,他意识到需要构建一套客观的工具——文体学,这是一个运用语言学知识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子领域。除了建立用于分析的理论和操作性文体学工具外,他还特别注重实证方法,从形式出发,设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和谐对应,旨在探寻阮攸天才之处,这些天才之处既非古人所学,也非其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潘玉对阮攸的赞誉在于,《金云翘传》的作者取得了前人未及、后人只能效仿的成就。凭借其对历史和社会的了解,潘玉指出,《金云翘传》分析中经常提及的“才智与命运相悖”这一核心思想,是黎朝末、阮朝初的当代社会问题,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曾提及,但阮攸将其概括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议题。我们需要记住,天赋与命运相悖的故事源于《金云翘传》。“[P. Ngoc 1985; 52]。阮攸的才华不仅在于构建一套基本的思想体系,更在于他能够生动地描绘情感的细微差别,构建严谨的结构,合理地展现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而非像清心太仁的《金文桥》故事那样简单地叙述事件,或者更广泛地说,不像中国传统连环小说那样。根据潘玉的分析,阮攸对人文主义概念(或哲学运动)非常了解,并运用佛教的思维方式;他甚至对多种文学体裁都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融合喃字叙事体裁、抒情体裁,尤其是戏剧体裁的对比,力求达到……”将《Truyện Kiều》提升为我们所知的第一部伟大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典范之作。”[P. Ngoc 1985; 198]。
为了对阮攸的才华做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评价,潘玉对自己的工作设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他将“独特性”作为研究所有比较的核心标准。从作品中的具体现象到确立阮攸风格的显著特征,整个过程都涉及频率的统计分析、与历史和时代的比较,以及与其他作家和杰作的比较。例如,在分析《金云翘传》中的诗句时,潘玉总是运用对比来得出结论。同样,计算诗句和意象的比例也体现了他所重视的定量方法的可靠性。有人认为,潘玉对结构主义的透彻运用及其极其严谨的形式分析,在当时(大约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的,但到该书出版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结构主义运动被语文学研究中更新的趋势所取代,其局限性已经显现出来。潘玉的研究方法的确以语言学结构主义为基础,许多分析甚至受到美国描述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尤其关注结构主义语言学运动中的形式。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潘玉在始终运用《金云翘传》的表达形式来理解阮攸的文风的同时,也拥有他自己的补充观点:……这种形式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好,而是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能成功地传达所选的内容。“[P. Ngoc 1985; 6]。显然,他以越南语言研究者的敏锐视角,理解语义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在关于阮攸语法的章节中,他对语义语法的解释反映了泰斯尼埃的语言价值理论,甚至反映了菲尔莫尔非常现代的语法结构。”[1]与此同时,潘玉无疑非常重视内容在所有具体形式表达之上的决定性作用。他成功地通过形式辨识内容,从而更清晰地理解了阮攸等天才作家及其代表作《金云翘传》中相应的表达价值。尽管对话和叙述方式——他总是热情地想要分享和表达所有最深刻的思想——仍存在一些瑕疵,但他运用知识超越审美感知,力图阐释文学现象的深层含义,从而开辟一条新的理解之路,这种努力若非博学而有洞察力之人,是难以实现的。

3. 20世纪80年代初,潘玉在文学院档案馆工作数月后,受邀前往东南亚研究所。在那里,他得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书……东南亚的语言接触(与范德阳合著,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出版)是具有开创性的开端,它“解放”了长期以来主导越南语研究的语言学方法,这种方法只关注语言的内部结构系统。在第一章中,潘玉介绍了语言接触现象,并再次提出要解释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词汇、语法现象等的随机、零散的借用。他从越南语和其他东南亚语言等非屈折语言中寻找答案,并证明双语研究方法是必要且有效的。针对东南亚地区的双语或多语方法具有客观依据。[P. Ngoc 1983;19],潘玉分析了地理距离、征服过程、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等多种原因。潘玉由此考察了汉越词汇组中越南语和汉语的语义接触,以及欧洲语法对越南语的影响,旨在解释越南人的语言敏感性。
在讨论汉越词汇语义的章节中,他从汉越词汇的词形和组合分类入手,考察了决定汉越词汇内容细微差别的各种关系,并指出:用汉越混合语写的故事似乎比用纯越南语写的故事更具学术性……主要是因为元素 B。[中文原意]它排在前面还是后面,取决于元素 B 的产出率高低。如果产出率低,意味着该元素产生的词语较少,那么该词的学术性和晦涩性就更高。“[P. Ngoc 1983; 180]”。潘玉在内容层面解释了同属孤立语类型的两种语言(例如汉语和越南语)之间的方法论接触,并引入了“多义性”的概念。多义性是语言学习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增加了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并影响语言习得。这一概念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语法方面,越南语对欧洲语法结构(特别是法语、俄语和英语)的模仿,是两种不同类型语言接触的一个案例研究,旨在展示这一现象对越南语现代化的重大影响。在越南语言学领域,他首次对越南语与欧洲语言接触前后的语法进行了比较,观察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区分,这要归功于“sự”、“việc”、“cái”、“đã”、“sẽ”、“rất”、“một”、“cách”等伴随成分;观察名词和动词,以及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是如何借助介词和连词的工具,逐渐形成层级结构的;此外,潘玉还研究了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转换(分类),特别是简单句如何演变为复杂的、多层次的句子,例如从句的扩展,或演变为具有多个成分执行句法功能的句子,以及句子结构如何不断扩展等等。潘玉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与越南语文本数据(一种非屈折语言)语义一致的语法模型。这一理念对于越南语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建议,无论是从共时角度分析越南语语法,还是研究越南语语法的历史发展。
潘玉用一本不足300页、分为三部分的著作,对其理解做出了重大转变。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多语研究——认为,如果想要真正研究越南语和其他东南亚语言的本质,就应该也必须用多语研究来取代单语研究。然而,在这背后隐藏着他对语言接触本质的发现,而这正是该地区人民的一个关键特征。与方法论的转变同时发生的,是潘玉研究领域的转变。他从文学语言学转向了文化研究。

学者潘玉与范德阳教授及作者合影(2009年)
4. 与那些先深入研究特定学科,再拓展到更普遍、抽象的议题(统称为文化)的研究者不同,潘玉始终坚持将文化研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拥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术语。这一点在他最杰出、最知名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越南文化,一种全新的视角。(本书于1994年由文化信息出版社首次出版,并多次再版)作为他后续文化著作的出发点,他强调了三个核心术语:关系,选择和折射率分析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当然是“文化”,但并非模糊不清;潘玉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了清晰的定义:文化的对象只能是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选择的模式中,表现为存在于所有领域中的独特折射。[P. Ngoc 1994; 114-115]。他证明,正是由于这种看不见的关系,人类才会将头脑中的东西(符号世界)建模为外部的具体物体和活动(现实世界)。[2]文化并非有形对象本身,而是连接它与人类智慧的纽带。正是由于这种联系,每个民族才会选择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潘玉借鉴物理学中的折射概念——光线穿过不同环境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偏折——来理解外部现象如何通过选择机制渗透到内部文化基础之中。至此,关于语言接触的思路似乎被延伸并扩展到了文化领域。除了识别对象之外,他的分析还围绕着一个任务:尝试建立一种技术操作来解释文化中的折射现象,更具体地说,是越南文化中的折射现象。潘玉所定义的操作理论,是寻找一种连贯且严谨的方法来解释某种现象的步骤,而不是提供普遍知识的叙述。他成功地解读了阮攸在《金云翘传》中所表达的思想,并初步尝试将其应用于越南文化的研究。

学者潘玉和他的妻子与黄氏珠教授、人民教师黎鸿三以及作者合影(2014 年)
《越南文化》一书从形式出发,深入探究这些形式的内容、价值和意义,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为越南文化认同的探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文化认同并非一种客体,而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融合并连接了来自众多截然不同来源的元素,却创造出一种奇妙的有机统一体……越南人是拼贴艺术的大师。[3][潘玉,1994;108-109]。潘玉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越南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文化接触是其显著特征。因此,越南文化的本质在于,它与众多主要文化来源进行文化交流,并在本土意识的“过滤”下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形成越南文化——一种复合文化。
当然,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或许并不如理论家所愿般完美,也无法立即满足学术界的期望,尤其是在文化这样广阔而细致的领域。然而,潘玉提出的总体系统性理念,以及他为将文化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合法的科学以解读越南人的精神世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足以使他成为越南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杰出人物。
5. 从认识论、辨析学和操作学基础来看,潘玉的著作承载着如此重要的研究假设,并由层层逻辑论证支撑,提出了如此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观点,那么他所获得的认可是否真正与其成就相称呢?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选择像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那样行事:默默无闻,不抱怨,也不提要求。一些观点认为,潘玉想要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具备儒家学者的品格,而且是一位来自贫困但勤奋好学、文艺气息浓厚的义安省的“固执”的儒家学者(潘玉总是自称是一位“固执的学者”),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而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总是会受到一种正当需求的驱使: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所有有品格和智慧的人来说,表达观点是人生的共同目标。
潘玉并不追求名利,更遑论财富,但他始终怀着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在谈话中,他经常提及自己的人生格言:过平凡而有意义的生活。“潘玉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出的问题至今仍能激发学者们的思考和辩论,并为后代继续探索和完善他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过上了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作者:杨宣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