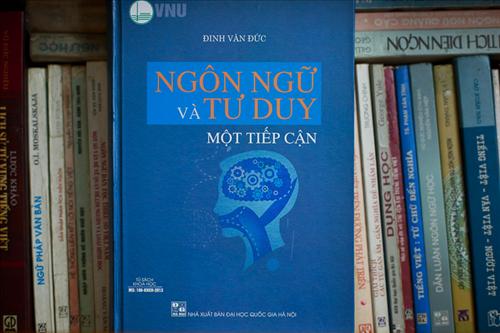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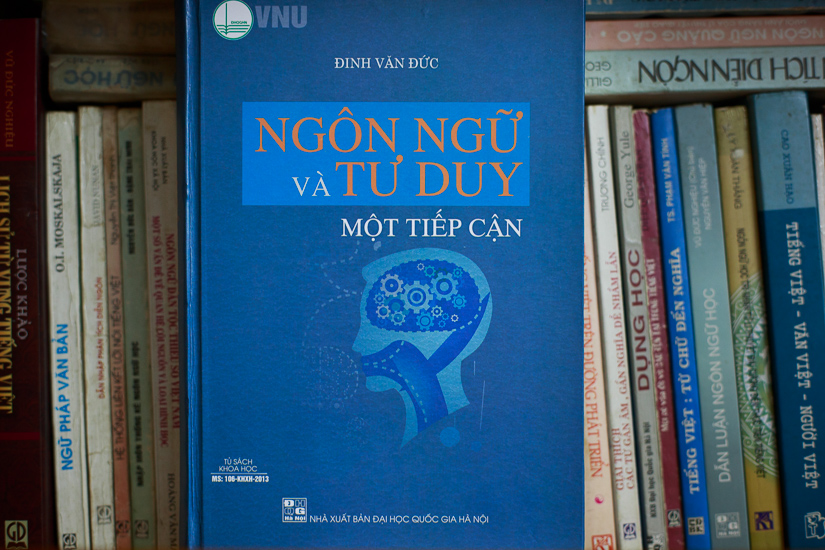
这本430页的书由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第四季度出版。(图片:Thanh Long)
正如其标题所示,本文开篇便提出,语言与思维是自古至今所有语言学理论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这是因为这种关系涵盖了语言系统的所有要素以及所有语言活动。此外,它之所以是核心,是因为只有理清这些关系,我们才能为理解语言学不同层面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奠定基础,这些问题涵盖了从结构到语义再到语用等各个方面。近年来,应用语言学(语言符号学、语言教育、语言信息服务等)的许多研究方法也都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
然而,由于语言和思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它们本身也十分困难、复杂、多面,显然难以系统全面地剖析和分析其规律和现象。我们的工作只是对这广阔领域做出的微薄贡献。

人民教师丁文德教授曾任语言学系主任。
关于这一问题的语言学理论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涵盖了逻辑学、形式主义和语义学等多个领域。事实上,没有一位语言学家忽视过这种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先确立自己的立场,才能着手解决其他具体问题。
20世纪初,弗朗索瓦·德·索绪尔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但归根结底,他最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观点背后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母语者在使用符号系统时的地位。这个问题也是尼古拉斯·乔姆斯基后期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乔姆斯基作为一名激进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始终没有放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体现在他的一些关键理论中,例如:普遍语法与特殊语法、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在语言习得中)、语言与意识、控制与约束、极简主义理论等等。
我们,本文的作者,自学习语言学理论以来,尤其是在攻读语言学研究生学位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系统地认识这个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年语言学和越南语语言学的实践经验。从最初的思考开始,我们就致力于寻找一种方法,并在1986-1987学年,也就是二十五年前,首次在本科阶段开设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课程(当时共有27名学生)。后来,我们又将这一问题提升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语言与思维”,并开设了第一届研究生课程(1997年)。在此过程中,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经历了多次变化,融入了更多要素,并发展出我们独特的研究方法。本文正是基于我们多年来的讲座,以及与同事、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在研讨会上的交流和讨论而撰写而成。
回首往事,我在准备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在苏联攻读语言学研究生期间(1974-1978),我遇到了我的导师,一位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安塞夫特连科教授(1907-1987)。这位杰出的乌克兰语言学家指导我学习普通语言学课程。这门课程内容浩瀚,难以面面俱到。他建议我选择涵盖所有问题的最基础的内容。他给了我一些入门材料,帮助我入门,不久之后,他向我推荐了安塞夫特连科的著作《语言与思想》(1867)。安塞夫特连科是19世纪末一位杰出的乌克兰语言学家,他的理论似乎接近辩证认识论(尤其体现在“词的内部形式”这一概念上)。坦白说,我刚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很多内容都没看懂。但是,在撰写论文(关于词类语义学)的过程中,多亏了作者的介绍和分析,我逐渐开始理解它们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对20世纪语言学相关理论的接触逐渐使我理解到,语言和思维在反映和表达功能上是高度统一的。然而,从现实世界到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智力会经历折射,每一次折射,语言语义都源于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既具有交际性,也具有艺术性。如今,语言不仅是世界的镜像,更承载着人类的诗意和情感。我们对语义的理解逐渐被这样一个原则所强化:语言并非直接表达逻辑,而是通过语义表征来表达。逻辑表达对错(真/假),而语言表达意义。这些语言意义的折射,无论在结构上还是用法上,都反映了母语者的文化思维。
阮泰干教授和曹宣浩教授提醒我们,我们对此问题很感兴趣。阮泰干教授说:“要小心,思维和语言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要过度简化它们;要谨慎,以免退回到17世纪的波尔-罗亚尔逻辑或19世纪初的逻辑推理。”曹宣浩教授曾坦言:“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国家仍然有些人过于简单化,犯下令人遗憾的错误,他们把语言仅仅看作是表达直接逻辑的工具,而忽略了语言本身所表达的意义。”我认同这种观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努力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来理解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1970年夏天,越南读者通过俄文译本了解到W.L. Chafe的著作《意义与语言结构》,该书刚刚在美国出版。在当时,这是一本从全新视角探讨语义学的罕见著作。曹春浩教授(1973年)为我们讲解了这本书,正因如此,我们在阅读时才意识到句法的核心在于语言的语义结构。直到1991年,我仔细阅读了曹春浩教授寄给我的《越南语——功能语法入门,第一卷》之后,才意识到语言和思维的重要问题不仅与逻辑表达式、功能词、语言层次、语言单位等——这些我之前教给学生的内容——相关,而且语言和思维深深植根于语言活动之中,植根于F. De.提出的语言与言语二分法机制之中。索绪尔在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学和诗学的著作中,进一步拓展到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语义学和实用主义。此后,另一部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是H.S.泰耶(1968)的《意义与行动:实用主义批判史》,这是一部从西方哲学视角出发的实用主义批判专著。从非实证主义的立场审视实用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北美和西欧实用主义者和符号学家的观点。这也为理解这些学者的语义立场奠定了基础,其核心在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对符号二元论和三元论(尤其是语言理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作用于不同本土文化背景下的实用主义研究。
事实上,本书仅触及语言和思维的几个关键方面,主要侧重于语法和语义。关于音系学的深入分析虽然原则上是必要的,但由于我们在该领域的理解和专业知识有限,因此不得不将其搁置。尽管将其单独列为一个更深入的主题,例如思维、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合适,但在此我们仅敢于探讨其中的几个方面。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语言和思维与母语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弗朗西斯·德·索绪尔理论精神的关键支柱:语言是母语者的语言,文化是母语者的文化,源于母语者的思维。母语者在语言系统中对思维和语言有着显著的影响,并涵盖了语言活动(即母语的使用)。我们力求在反思的一般理论框架内,对语言的创造性和艺术性折射过程,寻求一种独特的理解:从现实到母语思维,从思维到语言,从语言到语言类型,再到每种语言的语言使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条连续的路径,其中包含不同的折射,并因每种特定语言而有所差异等等。
多年来,我们陆续向本科生和研究生介绍这些主题,但每年的内容都不尽相同。我们努力更新信息,例如,早期我们更注重语言的结构方面,后来又加入了语义学和语用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越南语言学家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黄飞、杜友洲、李全胜、阮文协、陈文阁等学者以及其他同事的研究成果。必须指出的是,这一问题在内容和方法论上日益多元化,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然而,我们只精心挑选那些我们认为足够成熟、可以纳入大学课堂的内容,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与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和同事们分享我们的思考。作者们有机会交流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反馈,这些反馈让我们感到惊喜,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思路。最近一次富有成效的交流发生在我们与心理语言学专家李全胜教授和语义语法专家阮文协教授之间,他们两位后来都将研究方向转向了语言认知理论。本书最后一章正是在这种交流精神的指导下撰写的。
本书历经多年撰写而成。然而,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感到些许不满足,因为理论在不断发展,而语言实践却在持续演进。因此,我们在此仅怀着谦逊的愿望,呈现我们个人在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和见解,这份经验和见解源于我们对这一长期关注的课题始终如一的热情和执着。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同事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讨论,他们为本书的内容创作贡献了许多想法和方法。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们衷心感谢《词典编纂与百科全书》副主编范文廷副教授,他是一位在出版领域经验丰富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们还要向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将我们的这部力作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读者。
我谨借此机会向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语言学系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之情。我在这里工作了半个世纪,在系里任教,有机会定期介绍和分享我的学术思想。我深感荣幸,而且时至今日,这种分享仍在继续。
作者:教授、人民教师丁文德
最新消息
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