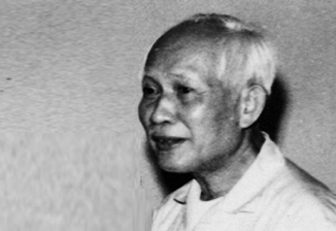
1960年,我读高三。
有一天,在我居住的那所位于省里的初中宿舍里,隔壁住着一位文学老师的妻子,她给丈夫带回了一本新书。她是一位书商。看到新书,我急切地问老师:“叔叔,这是什么书?我可以看看吗?” 我把书拿在手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一卷”,作者是黄春二。巴叔解释说:“黄春二先生和我来自河静省,是黄春汉先生的亲戚,黄春汉先生现在是河内郊外一所大学的教授,拥有德国文学学士学位。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书。”几天后,他把书借给了我,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我第一次通过书中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作家的名字了解了俄罗斯文学的概念,至今我还记得作者翻译的普希金的那首诗:
我爱我的祖国,一种奇特的爱。
但我的理智始终无法抗拒它。
古代的神秘传统
一种充满自信的沉着。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一年后(1961年),我被文学院录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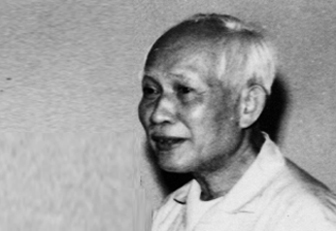
黄宣二教授
开学伊始的一个雨天,我在黎圣宗街19号的主讲堂第一次见到了倪教授。当时校长阮如坤岱正在介绍各位院长。他站起身,转过身,微笑着回应。我们也跟着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一头银发,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笑容温和。他身穿一件白色三口袋短袖衬衫和卷起裤脚的蓝色工装裤,朴素却不失优雅。那一年他47岁,刚刚被任命为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文学+历史系)院长,此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有邓泰梅教授、陈德草教授和陈文耀教授。他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心中教授和院长的典范。他的形象也激励着我,让我有幸在职业生涯中践行并努力追求这些价值观。但那还要再过35年……
入学典礼结束时,教授带领新生参观图书馆(现为黎凡添礼堂),并说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同志们,跟我来。”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未见过哪个老师称呼学生为“同志”。但他一生都这样称呼我们。
大学的阶梯教室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最令人惊讶的是那里浓厚的学习氛围。虽然许多人穿着棕色长裤和布衬衫,有些人甚至光着脚,但我们学生的热情和决心丝毫不减。除了Nhi教授、Bach Nang Thi教授、Hoang Nhu Mai教授、Le Dinh Ky教授、Dinh Gia Khanh教授和Do Duc Hieu教授这几位四十多岁的教授之外,系里的其他教授都比较年轻,而且对学生很友好。
从老师那里我们了解到,Nhi先生来自河静省的一个贫困村庄。他从小就勤奋好学,高中毕业后获得奖学金前往法国和德国留学,最终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的法语和德语都非常精通。他曾翻译过……战士妻子的哀歌他会说法语,并因此受到表扬和奖励。反法斗争爆发后,他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返回越南,加入了南方的抵抗运动。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一直在南方地方委附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来成为南方教育部的重要干部和部长,之后调往北方。有一次,我去上课时,看到他戴着一个奇怪的徽章,不是勋章或奖章。我问了他,才知道那是一个“徽章”。祖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我非常荣幸能将此徽章颁发给那些参与了越南南部长达九年的抵抗运动并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们。文学系还有一位拥有这枚徽章的人:阮咸阳教授,他曾是当时从泰国向第九区运送武器的‘无编号’船只上的士兵。”
倪教授并没有立刻给我们上课。直到我们大三、大四,他才开始给我们上两门课。不过在此之前,作为院长,他经常利用自己的威望邀请许多知名学者来给我们讲课,比如邓泰梅、曹春辉、武玉潘、怀清、辉干、春妙、车兰园等等。正因如此,我们才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实用技能。作为学生,我们不敢直接接近他;只有在需要得到许可的时候才会去他的办公室,或者在走廊里闲逛,看他和他的助手潘卓景(后来在河内八丹街5号开了一家著名的二手书店)打台球。他常常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挥手致意。
当时,文学院位于朗村,校园环境清幽宽敞(原址属于两所大学:现在的对外贸易大学和外交学院),尽管生活贫困,却为学生提供了舒适的生活、学习和活动环境。在我们两年的学习期间,倪教授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和专业课:苏联俄罗斯文学和美学批评这位教授将 18 至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交给了一群年轻的教授:阮金定、阮长历、张光哲和裴春安。
第一天上课,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授课老师是系主任。然而,他却显得沉着冷静。他仍然穿着去年那身传统装束:一件有三个口袋的短袖衬衫和一条蓝色工装裤。他轻轻地用手中的烟斗敲击着金属烟盒。他慈祥地看着我们,轻声说道:“我想利用这第一节课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他并没有从学术层面谈起,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开场。他告诉我们,我们成长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完全理解那些失去祖国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前的一个巴黎新年夜,一群国际学生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祖国的故事。然后,他们请每个人介绍自己的国旗并演唱国歌。轮到他时,他却慌乱而沮丧。他的祖国已经沦陷,他还能介绍些什么呢?他强忍着泪水,给我们讲述了村里节日上竖起的旗帜,还唱了一首来自义安省和河静省的民歌。同学们鼓掌,但他却泣不成声。我们班顿时鸦雀无声。
教授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努力学习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因此,你们必须提高自学能力,培养外语能力。缺少这两点,你们就无法进步。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背诵《拉鲁斯词典》以便自学阅读和翻译书籍,以及在寒冷的冬夜里,为了保持清醒而将双脚浸入一盆冷水中学习的经历(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背诵了阮南安的俄越词典——这位学生后来成为了才华横溢的诗人英玉)。他自学了半年俄语,然后阅读并撰写了俄罗斯文学史,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他当时对我们这群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说实话,这位教授和黎廷基教授一样,口才并不出众,但他语调舒缓、娓娓道来的讲课却见解深刻,分析透彻,信息丰富。他对高尔基及其短篇小说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母亲,猎鹰,丹·科的心……索洛霍夫笔下人物的历史悲剧顿河静静流淌,大地荒芜,人类的命运已然注定。……这些都是真正新颖而令人难忘的事情。在教授俄罗斯文学时,凭借他对西方文学的渊博知识,他总是将俄罗斯文学与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文学进行比较分析。通过他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莎士比亚的英语诗剧之所以能被改编成法语和德语作品,要归功于查尔斯·雨果(维克多·雨果之子)和德国诗人斯莱根的才华。
在讲授现代美学批判时,我们的教授总是引导我们从古希腊美学出发,途经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现代,甚至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美学。有一次,他问我们: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吗?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永远翠绿。“?”我以为是某个哲学家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回答说:“这是歌德的名言。”老师说这句话没错,但翻译不准确。然后他解释说:“这是歌德史诗《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赞美女性身体之美时对医生说的话。原文不是‘永恒的生命之树’,而是‘金色的生命之树……’。”学习需要练习,所以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分析艾特玛托夫的《山与草原的故事》中两篇短篇小说——《第一位老师》和《戴红围巾的小枫树》——的美学内涵。在老师给我们评分之前,我们进行了几次研讨会,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想法。
在学术上,他始终坚持正统观念,与年轻的黑格尔学派或加罗迪、卢卡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非常严谨,原则性很强。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后来成为组织部门的一名官员)因为在教授讲解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时笑了,而被要求离开教室,并且不被允许继续学习。他出的考试很难,而且评分非常严格。
我的学生时代在战乱中结束(1965年)。我留在学校担任教职人员,在我的教授指导下工作,但专业方向不同:语言学。学校不得不从河内撤离到太原省大慈县越北山区。我们,无论老少,都跟随他开始了新的生活。到达营地后,他很快适应了战时生活,放弃了在河内骑了很多年的那辆熟悉的西姆森摩托车。他和我们一起挖隧道、盖竹子和茅草屋,在油灯下读书。他始终保持着冷静、沉着和乐观。一天,在领取大米配给时,正值暴雨引发洪水,他把装满大米的背包放在一头水牛背上,让学生们抓紧,好让水牛游过河。这个故事后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K8班的一位学生写道:疏散叙述“我为老师写了一章题词:‘黄主席骑着水牛过河’。”
我们几个老师,包括Ham Duong老师、Thuat老师和我,住在Nhi老师家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所以我有机会和他家人住得很近。他也积极参与农耕和畜牧。他说:“我已经习惯了。在沼泽地里待了九年更难,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们经常和他交换农产品(蔬菜、鸡蛋、葫芦,有时甚至还有鸡)。他指导我们用新鲜木薯(要先煮熟切片喂鸭子)养鸭产蛋。他比我们更擅长捕鱼,因为他熟悉越南南部的运河和水道,所以能改善我们的伙食。尽管生活艰辛,他总是鼓励我们认真读书学习,自己也坚持学习写作,包括创作了话剧《Kieu》。K8学生表演艺术团曾在各地演出,甚至在河内也表演过这部话剧。
然而,倪教授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他还是系主任,肩负着许多责任。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的同事们都非常尊敬他,希望他能专注于本职工作,因此他们都尽力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我记得副院长们:张文荣、黄友彦、孙嘉银、阮文慈、杜德孝,以及助理们:潘泽景、阮春花、裴庆世、阮玉山……他们都为他辛勤工作,有时甚至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疏于处理细节。我记得,1972年夏天,战争十分激烈,美军轰炸不断,学校和系不得不再次搬迁到河北县协和市。有一天,我给他送去了工资。他收下工资后问道:“你知道我们系现在在哪里吗?我想去拜访你们。”我当时有些惊讶,但立刻明白了,便把情况告诉了他。第二天凌晨四点,教授就骑车一路北上,去探望同事并视察系里。还有一件事。回到大都后,有一天我去他家用米换面,他对我说:“年轻同志们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我经常参加会议,但很少见到你。”我解释说:“先生,我不是党员。”他平静地回答:“哦,真的吗?那你一定要更加努力。让我来介绍你们认识吧。”我连忙说:“不行,先生,这不可能。您在不同的系,我在语言系。”他回答说:“为什么不行?我是党员,而且是这里的领导,为什么不行?我认识你们所有人。”我默默地道谢,但不敢再多说什么,怕得罪他。
尼老师是个善良诚实的人,但个性很强。关于他,我有很多趣事,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比如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宴会,饭后他会把剩菜剩饭收起来分给同事,解释说:“他们给了我,所以是我的。”还有一次,他出差途中停下来喝水,站在店外没进去,而是对同事说:“我这儿有瓶水,你们进去喝吧,然后我们凑钱付账!”还有一次,杨老师看到他家有个葫芦架,就让我过去“联系”他。尼老师带我到葫芦架前摘了一个葫芦,然后又让我再摘一个。我选好指着,他又切开一个葫芦说:“第一个我给了你们,但这个你们得付钱。”后来,当我有机会在欧洲生活时,我才明白他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式,一切都很透明,既不爱社交也不爱装腔作势,而且一点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吝啬。
1984年,教授七十岁生日时,我们系在禄德宿舍餐厅为他庆祝。那时生活十分艰苦,只有香蕉、糖粉和茶。教授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马江兰先生恭敬地向教授致意:
让我们举杯纪念这一天!
老师,我们举杯庆祝您八十岁生日。
但是……他78岁时就停止了工作。
在黎圣宗大街的主楼向老师告别时,我脑海中浮现出革命家黄国越的身影,他身体虚弱,需要两个人搀扶,却依然努力前来致敬。随后,同样虚弱的陈大义教授也来向他从巴黎归来的朋友道别,他们一起回到越南加入了抵抗运动。
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文学系缅怀他,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和系主任,在他系成立之初就给予了他指导,他是整整一代人的榜样。
2014年马年夏季
作者:教授、博士、人民教师丁文德
最新消息
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