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走得很慢,偶尔停下来等身后跟着一位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年轻女子。班委会里一位年纪较大、经验更丰富的成员指着老师喊道:“那是黎廷基老师!黎廷基老师和他的妻子!”我们都朝那个方向望去。我默默地比较了一下他们: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得多。后来,从疏散地回到河内后,我有机会去C1栋——美池宿舍——三楼的一间小房间里拜访他,那时我才知道他妻子的名字叫龙,我称呼她为龙太太——而且她的长辫子已经不见了……
我记得那位教授,身材矮壮,面容沉思而沉静。他说话轻声细语,仿佛在自言自语。他很少微笑,但一旦露出笑容,便是灿烂的笑容,眼神空灵而闪亮……我偶尔会跟随朋友们去拜访他,静静地观察他。以前我并不知情,但自从认识他之后——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后来他成为我的讲师——我注意到,围绕在他身边的并非女学生中那些美丽的女孩或年轻貌美的女子,而是一群系里特立独行的“猩猩”,他们的穿着、举止,甚至言谈都别具一格。他热情地接纳他们,而他们也热情洋溢地与他交谈,而且“非常民主”。他们吟诵诗歌,有时双眼半闭,陷入沉思;有时低声细语;有时高声呐喊,手舞足蹈,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他认真地倾听,饶有兴致地忍受着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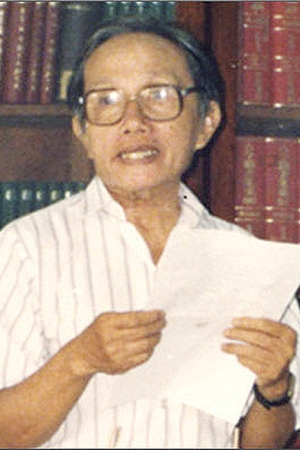
黎廷基教授
我记得直到大四我们才开始学习专门的课题:《金云翘传》和阮攸的现实主义——这个课题被收录在一本书里,非常引人入胜,而且,简单来说,百读不厌。这不仅是文学系学生的普遍感受,也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辛女士——经济与计划大学的毕业生,黎志勇教授的妻子——当时是文学系的一位年轻讲师,与黎志桂教授、阮天甲教授和丁春勇教授是同一代人……她就是《金云翘传》的忠实读者。因为黎志勇教授是我的班主任,而且他也来自广平省,所以我偶尔会去他家。有一次,我看到辛女士手里拿着一本《金云翘传》和阮攸的现实主义。她一边读一边热情洋溢地赞叹道:“秋,Ky先生写得真好!我读过很多遍了,越读越喜欢。Dung先生的书里有些地方我看不懂……但是Ky先生的书,我读着读着就明白了,而且觉得很精彩(如果我尊敬的Le Chi Dung老师看到这些,我真诚地希望他能原谅我)。Ky先生真是个天才。”突然,她的热情消退了,语气变得若有所思:“Ky先生现在的工资够我们每周买一只鸡来改善一下饮食了,是吗?”……
除了他那部曾名噪一时的专著之外,这位教授还撰写了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如《艺术方法》(1962年)、《文学理论基础》(1971年、1984年),以及文学评论和研究论文,如《诗歌之路》(1969年)、《与宣妙、怀清、车兰园共赏诗歌》(1988年)、《现代诗歌——起伏跌宕》(1989年)等等。他的强项和优势在于诗歌的研究和评论。无论是评论一位作家,无论其资历深浅、成名已久还是刚刚起步;从杜友到范天燮,从车兰园到泰江,从德行到刘光武……(《诗歌之路》),他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倾注了全部的思想和情感,以清晰的思路和敏锐的直觉进行写作。他的作品始终具有开创性,这得益于其精湛、细腻且深刻的写作风格。特别是通过像卢、卢仲卢、宣耀、辉干、韩麦子、阮平、车兰园、武黄章、碧溪……(新诗——起起落落)这样的代表人物,黎廷奇教授复兴了20世纪越南诗歌潮流中一个辉煌而独特的诗歌时代。
或许是因为他性格内省,他的讲课“含蓄而非激情澎湃”;又或许是因为他试图引导听众——学生们——深入探究主题的内涵,而较少关注课堂上的兴奋气氛,或者更在意“年轻稚嫩”的学生听众的外表,因为他们往往更关注老师的穿着打扮和举止,而非讲课内容本身。如果认真聆听Ky教授的课,并拓宽自己的“预期”,就能收获许多有益且新颖的见解。例如,在讲解《金桥传》时,当阮攸描述“民族美人和天才”金仲与翠桥的相遇和亲密接触,以及“两人目光交汇,畏惧地低下头”这句诗时,教授停顿了很久,解释并阐释了阮攸在刻画一对深爱彼此的恋人(其中还带有一丝“暧昧”)方面的精湛技艺。我的老师说,当一位贤淑的女子与一位倾慕她的男子对坐,当男子“直视她的脸庞”时,女子应该“羞涩地低下头”,因为在那一刻仰视他是不合适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老师这些既幽默又深刻的分析。我“意识到”,阮攸确实为翠桥这个角色,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和私密的场景中,选择了一种非常优雅、极具东亚特色的姿态。
1976年12月,多亏了当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所大学任教的语言学教授阮来教授的安排,我的老师出国旅行不到一个月。那时我刚结婚,正为找不到住处而发愁。老师把我叫过去,说:“人生只有一次,来我家住吧,我家明亮宽敞。我要去德国大约三个星期,宿舍和行政办公室一定会给你安排住宿的。”我非常惊讶,只能低头表示感谢,强忍着即将涌出的泪水……从德国回来后,老师看着房间,感谢我帮他打扫整理。他弯下腰,突然说道:“哦,你帮我洗衣服了?上次我去南方的时候,把一套类似的衣服泡在盆里,等我拿出来的时候,都烂透了。” (那时,龙女士已经搬去了西贡,老师独自一人住在河内。)他回忆说,他在德国买了几十根辐条,欣喜若狂,因为这种东西在越南非常稀缺。他惊讶地发现这些辐条是儿童自行车用的(我想那时候还不叫迷你自行车),而他自己并没有一辆。接着,他摘下一个红润芬芳的苹果,小心翼翼地切成许多片,放在盘子里,配上诗意优雅的邀请:“来,尝尝来自遥远西伯利亚的美味……”那是我当时尝过的最美味的水果。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苹果!
我记得黎廷奇教授为人真诚朴实,厌恶一切形式主义、浮华浮华或肤浅的东西。虽然我在河内大学文学院的时光短暂,却充满了他的悉心指导,让我得以迈出踏入我如今热爱却又曾令我畏惧的职业的第一步。我的第一次观摩课,也就是他们给我讲课反馈的环节,出席的都是一些知名人士:黄如梅教授、黎廷奇教授、潘居德教授、何明德教授……站在讲台上,我心跳加速,双腿发抖;我说话结结巴巴,犹豫不决。课后,黄如梅教授悄悄对黎廷奇教授说:“他讲课就像学生在跟老师对话一样!”我暗自佩服黄如梅教授的敏锐洞察力。那一刻,我的确忘记了讲课内容、原定的演讲顺序,甚至忘记了坐在我面前的几十名学生(其中不乏几位从战场归来的老兵,我平时对他们十分敬重)。我的眼中只有教授们高大的身影……但我敬爱的教授们个个都是“高尚之人”,他们给予我真诚而宝贵的反馈,帮助我更有信心面对未来漫长而艰辛的道路。Ky教授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指导。他教我如何阅读和记笔记,如何“双脚并用”——既要兼顾教学又要兼顾科研,尤其要教我如何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同时,撰写重要的研究论文。我的教授特别强调并反复提醒我:“你必须记住,写诗歌评论非常难,但最难的是隐藏理论,让它融入分析感受之中。”他还补充道:“没有什么比写理论完全暴露、枯燥乏味、僵硬刻板的诗歌评论更尴尬的了……”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和评论文章中所获得的一切,都源于这些宝贵的入门课程,源于教授深刻的经验和“哲学”。他的关心和指导往往并不“过于戏剧化”,却蕴含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帮助研究者做出恰当的选择。更深层次地讲,它是一种诗歌评论研究的美学,一种文化修养,一种对待诗歌(尤其是文学)的“公平”之道。
因为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每次我去他家,总能看到他埋头苦干,书桌前堆满了书籍和参考资料(但依然井然有序,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每当有人质疑这凌乱的景象时,他都会这样解释),所以他总是非常忙碌。准备饭菜的时间也是他唯一可以“放松”(他开玩笑地这么称呼)的空闲时间。即便如此,他从不吝啬与人探讨专业问题,以及他感兴趣的作家和作品。在那些时候,他显得更加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平时沉思的神情也变成了轻松的笑容。在一次这样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一篇题为《青年、革命与诗歌》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段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文字,描绘了长山——那一代反抗美国、拯救国家的诗人的摇篮——的艺术景象,而我对那里非常熟悉:“长山在暴雨和洪水中,在烈日和老挝的狂风中,在隆隆的炮火和子弹中……”听到这段文字,黎廷基教授平静地回答说:“啊,我是从一位即将毕业的警校学生那里‘偷’来的。我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你必须与长山同甘共苦,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我明白这只是一种比喻,而教授的真诚让谈话变得越来越有趣,也越来越感人。不仅是我,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与黎廷基教授交谈无需任何伪装,也无需斟酌字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对话总是唤起我对一段温暖无忧时光的回忆。那些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
我记得,当我从遥远的西贡接到博士论文题目——《透过诗篇》和《送香入风》探究宣耀在1945年八月革命前的诗歌——时,我的导师寄给我几本书(其中《新诗——起起落落》和《与宣耀、怀清、车兰园一起读诗》成了我阅读和思考的必备工具)。他还提醒我要深入思考,不要重复他人,要找到“宣耀自我”的独特色彩,以及新诗中自然与灵魂的对比,与1945年后革命诗歌中自然与国家的区别。得知何明德教授接受我做他的论文导师后,他说道:“太好了。德教授在这个领域学识渊博。题目很好,但写起来并不容易; “你必须非常努力。”在正式答辩之前,我把论文摘要发给他阅读,并焦急地等待着这位新诗研究权威专家的权威评价。出乎意料的是,教授很快就读完了,并通过传真发来了一份评论,其中包含着赞扬和鼓励的话语。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对我来说,他能阅读我的作品就已经弥足珍贵;我从未想过他会为我写评论。我激动得哽咽,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他似乎为这位昔日学生取得的初步成功感到非常高兴。然后他问我发表了多少篇期刊文章,建议我先分批发表论文的部分内容,然后再出版专著。他还说我需要写更多文章,因为无论我是否愿意,既然我已经获得了大学教职,完成副教授学位(当时还不叫博士)就意味着要准备副教授的申请……现在,我坐在这里重读着1995年10月24日的评论,上面字迹细小而倾斜……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把它当作珍贵的纪念品。每当想起他曾经的教诲,我的眼眶都会湿润。我无比感激我的老师,却从未有机会报答他……
我本应有机会参与其中。教育出版社当时有一个编纂教授文集的项目,文学系主任阮氏贝女士盛情邀请我收集手稿、甄选作品,并为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一个表达我对教授感激之情的宝贵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最终在胡志明市出版。当时,我深感遗憾和难过,但客观地说,我认为胡志明市越南国家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工肯定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与教授关系密切,与他朝夕相处,更了解他。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2009年10月的一天,他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我心中,黎廷基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博学优雅,情感细腻深沉,思维敏锐,直觉独到。在我心中,他是一位慈爱宽厚、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宽容大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高尚、温暖、亲切的师生情谊之中。那是一个宁静祥和、充满生机与人情味的空间,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在我心中不断涌现,温暖人心。
河内,2014年4月11日
作者:副教授李怀秋博士
最新消息
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