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个人似乎非常幸运,仿佛天生就是当官员或领导者的料。事实上,他接受的是文学讲师的培训,因为就他的品格和专业才能而言,我百分之百肯定范光龙具备成为一名优秀文学教师的潜质。然而,1975年从文学院毕业后,他被留校担任文学理论系讲师(他的毕业论文实际上是关于外国文学的),但并没有太多教学经验,就被派往俄罗斯攻读研究生(研究课题同样与外国文学相关)。1984年返回越南后,他于1987年离开文学院,担任理学院副院长。此后,他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直到 2013 年 6 月,他辞去了河内市文化局局长的职务,回到文学院,像他所有的同事一样从事最普通的工作——教文学——他才真正成为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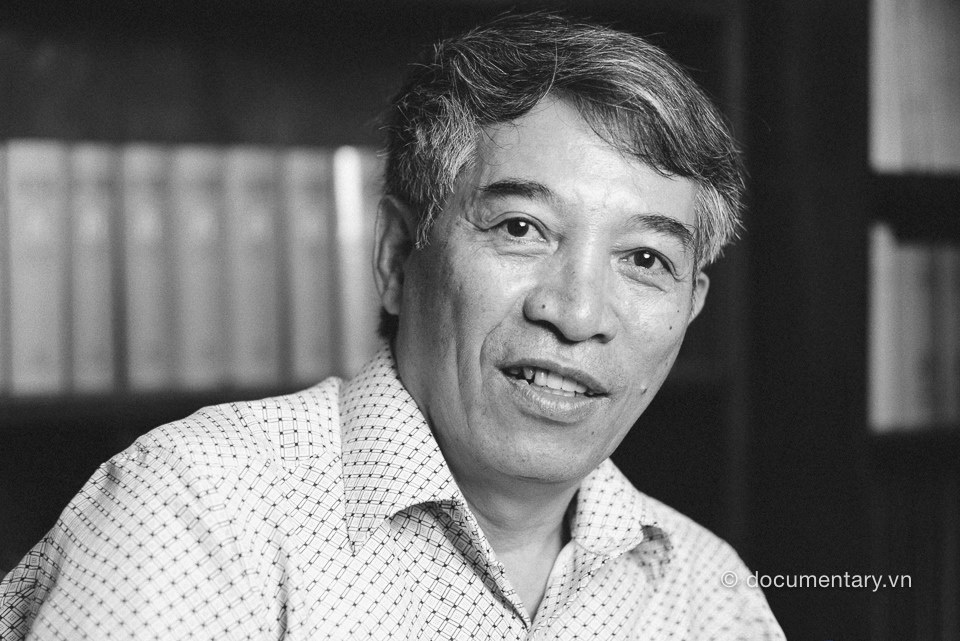
副教授范光龙博士/摄影:Thanh Long
他曾任文学院院长(1992-1996 年);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副校长兼校长(1996-2001 年);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2001-2005 年);河内市文化局局长(2005-2013 年)。
谈到范光龙副教授的行政管理经历,说实话,我了解不多。我和他更像是朋友,而非下属或上级,我们关系并不亲近,所以我无法“了解”或“干涉”他的私事。他接替阮金定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时,我只觉得他工作热情,待人友善,善于倾听,而且谦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范光龙出身于青年组织。学生时代,我知道他曾多年参与青年支部活动、跨支部活动以及班级委员会的工作;毕业后,他仍然是一名讲师,同时积极参与青年组织和社团活动——我知道文学院很少有老师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因为它会占用他们大量的私人时间。但出身革命世家(父亲是烈士,母亲是越南英雄),范光龙先生勤勉尽责地完成各项任务,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犹豫。我想,这正是他赢得信任和尊敬的原因。在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范光龙先生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整顿一个系,改进另一个系。虽然难以取得什么“重大突破”,但我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文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大约在1992年至1995年,也就是国立大学成立之前,作为原综合科学大学的一个院系,文学院仍然被视为一个规模庞大、享有盛誉的院系,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历史学院或数学学院。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年轻,而且刚刚开始管理文学院这样一个庞大的院系,范光龙副教授仍然成功地保持了文学院在校内外其他大型院系中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院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贡献。因此,他更加受人信任和尊敬。
从副校长、校长,到河内国家大学副主任、河内市文化局局长,我了解到,范光龙在更高的管理层级上始终保持着对教学的热情和对职责的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公共利益服务,从不畏惧承担任何任务。但或许正因如此,他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我说“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只是:很多人都说范光龙为人正直、坦诚、敏感。他只适合在工作量适中、人手不多且下属关系融洽的地方担任“安全”职位,比如文学院,或者像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这样规模较大的机构。如果他能在理解他性格、或者氛围轻松自在的地方发挥自身特质,他就能做得很好。如果“强迫”一位文学教师,即便身居副主任之职,也要尽快就诸如“土地清理”之类的具体事项直接思考和行动;或者让一位(与河西省合并后)位高权重、夸夸其谈却鲜有作为的河内市部门主管去“看守”和“监督”章美县的簌显寺修缮工程,即便他拥有“百手百眼”,也很难避免犯错。事实上,许多人都承认,范光龙在担任河内国立大学校长或河内市文化局局长期间,是一位真正尽职尽责的人。在担任文化局局长期间,他做了很多事情。以下是他本人在接受《安宁世界安全》杂志女记者采访时讲述的一个小例子:“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我担任局长时组织的一次河内文化展……一些资深顾问告诉我,河内文化展一定要有人力三轮车,因为人力三轮车与河内文化有着悠久的渊源,甚至可以被视为河内的象征。但我不同意,我认为人力三轮车的形象只会让人联想到艰辛劳作,并不能象征河内文化的精髓,所以我为这次展览选择了‘文学文化’这个主题。”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足以证明,尽管范光龙并非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但当他被委派任务时,他其实并不陌生于他之前的职业经历(大学管理和教学)。范光龙能力出众,他并非“碰运气”。但我知道,在范光龙先生近十年的河内文化管理工作中,以及他在河内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和越南国家大学的管理经历中,他都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实际贡献的多少取决于具体情况、他人的支持与合作,以及集体的评价。还有一点我明白,也想再次强调:由于他的坦率、正直,甚至有些火爆的脾气,“管理者”范光龙先生有时会招致一些人的反感,也会让另一些人感到不满。甚至有时,我也会因为他“过于极端”的性格或“过于善良”而对他感到不满。诚然,极端主义有时会导致僵化,甚至会毁掉一些事情。但我也认为,“人无完人”,又能怎样呢!范光龙先生并非天生的管理者,不是吗?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还有另一项工作,在我看来,完美契合了他的优势:范光龙不仅教书、搞研究,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如果他能从职业生涯伊始就坚持发挥自己的优势该多好?不过话说回来,又有多少人能“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呢?范光龙就是这“稀有”之人。谁知道呢,或许正是这些年来他在各种管理岗位上的经验,尤其是在河内负责文化事务的那段时间,磨砺了他的写作技巧和人生阅历。如今,他又回归了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可惜的是,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他已经重返教坛。我知道,范光龙老师深受许多学生的敬仰。教授文学理论或许是他的强项,因为他思路清晰、口才极佳。尽管与何明德教授或文学系其他一些老师相比,他的声音略显逊色,但我仍然觉得范光龙的文学理论课对学生极具吸引力。曾几何时,出于好奇,我甚至想找个地方偷听他的课,以验证学生们的赞誉是否名副其实。但还没等我付诸行动,他就被提拔到行政岗位,教学时间也随之减少。虽然减少了,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因为我知道教学是范光龙老师的挚爱。说他因为行政工作而忽略了科研,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纵观范光龙副教授的研究著作,我们或许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专著(例如专著),但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却相当可观。更不用说他在河内担任文化行政官员期间,定期在报纸上发表的数百篇文化评论文章了。此外,他还以中央理论委员会代理秘书的身份撰写了许多关于三十年文化改革总结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往往鲜为人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范光龙的真正强项在于:在他担任河内文化行政官员期间,他充分发挥自身人文研究的优势,创作了数十部戏剧作品,其中许多都曾搬上舞台演出,一部作品更是荣获2005年全国戏剧节一等奖。范光龙的戏剧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一位博览群书、观察入微、思想深刻的教师的“内在动力”,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涵盖了历史与当代。这些是剧本……高八季、阮公治、国家债务、胡志明时刻、扮演角色、海归、人面恶魔、督察……这些都是棘手的话题。我曾问他:“你这样写,不怕得罪人吗?”他没有回答,但我知道,他内心那个自由坦诚的人该开始“挣脱束缚”了。当他能再次做回自己时,就无需再如此“矜持”了。有些人为他担忧,但我认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锤炼”,范光龙绝不会“愚蠢”到打破他既定的“原则”。因为,看清时代的讽刺,像范光龙这样如此执着的人,又怎能保持“沉默”呢?他告诉我,他目前有三部手稿即将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目前正在接受文学评论家裴越胜的评论);以及一项他长期思考和酝酿的关于越南文学现实主义的研究项目……
要完整地“描绘”范光龙副教授的形象,肯定需要一篇长文。以上仅仅是一个远观者的简要概述。而这种远距离的、粗略的观察只能揭示一些“问题”。我不敢说已经描绘出了他的全貌。因为我相信范光龙仍然拥有许多我们尚未完全发掘的潜能。正如范光龙曾经研究过的作家阮明珠所说:每个人心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美丽和奇妙,以至于一生都可能无法完全发现它们。范光龙就是这样的人。
|
副教授,范光龙博士
+ 工作地点:语言学与文学学院,现为文学学院。 + 管理职位: 文学系主任(1992-1996)。 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副校长兼校长(1996-2001)。 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2001-2005)。 河内市文化局局长(2005-2013)。
文学理论,教育出版社,河内,1995年,合著 回想起诗歌的黄金时代,教育出版社,1993年,合著 为河内制定文化战略。,科学会议论文集,河内出版社,2005 年,合著。 在河内推广专业戏剧表演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科学会议论文集,河内出版社,2006 年,合著。 基于历史视角的文化理论创新。,科学会议论文集,河内出版社,2006 年,合著。 |
作者:陈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