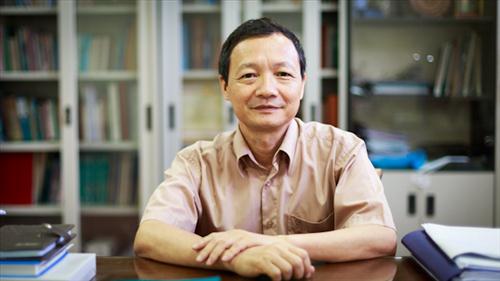
他出生于马年(1954 年),我出生于羊年,比他小一岁,比他晚一年在河内大学文学院学习。
能与你相伴,成为你的朋友,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我已年过六旬,却依然毫不掩饰这一点。人与人之间相依为命,彼此映照,如同镜子。看着年幼的孙辈,我们仿佛重温了童年;看着老师的人生,我们又会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朋友之间,彼此凝视,汲取着无数宝贵的人生经验。
有时我们聊天时,我会开玩笑说:“我们有相同的命运,但你是金沙忠,而我是金沙忠——这样更准确。”
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学习他那坚定不移的人生哲学:“力求善良”。仅此而已,却如此艰难。的确很难,但必须如此。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适合诗歌。即使是乡巴佬也能成为知识分子。武德义教授出生于交水郡交田村一个儒家家庭。高中时期,他在当时著名的南方地区文科成绩优异,并于1972年考入河内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 Vu Duc Nghieu
他被分配到语言学专业学习。第一届只有21名学生,入学时正值美军轰炸行动进入最激烈、最关键的阶段。在河北省协和县安峰的疏散营地,他的朋友们——都是来自农村的——渐渐地喜欢上了“爷爷”阮先生。他身材矮小,皮肤苍白,偶尔会捉弄穿着紧身衣服的女孩们。有时,“爷爷”会使用一些深奥、古老而又充满乡土气息的成语,引得大家认真聆听,不禁发笑。当时,很少有人理解这门学科的深层含义。毕竟,这都是文学;他们来自农村,只能服从组织分配的学习任务。“我们为了革命而学习,兄弟姐妹们/我们为了革命一起挨饿,没问题,”他们常常这样开玩笑。。
课堂上,每位老师讲的第一件事都是:“暴风雨与越南语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我当时觉得他们只是在故弄玄虚,但后来我花了毕生精力研究语言学,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逻辑。即便活两三辈子,也未必能完全领悟这句谚语的含义,而它或许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武德义教授是老一辈中少数几个在语言学方面迅速取得突破的人之一,并受到前辈大师的信任,将科学知识传授给他们。
我开始亲眼目睹这一切。1976年,我在水塔边遇到他,问他:“你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什么?” “我在研究反向词典。” “那是什么?” “它不是正向词典。”!”“你是倒着说吗?” “不!是反过来复制。比如,EAT这个词,先写N,再写Ă。然后按字母顺序排列,组成一本字典。” “真是浪费时间!” “只是随便玩玩!” 我的导师是阮德丹博士,一位英俊的数学家兼语言学家,他从波兰回来后经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奇怪的方法一窍不通,但我暗自佩服导师选对了学生——他做事一丝不苟、严谨认真,而且一直在钻研研究资料。通过他,我才明白K3或K5打孔券是什么,并暗暗赞叹西方人比我们强多了。后来我们搬家的时候,有三个抽屉装着大约一立方米的打孔券,我们费力地把它们带在身边。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张,但我开玩笑说:“丢了两个月的油票纸够煮一锅米饭了。”
那份反向词典手稿还在那里(整整七十捆七分钱的纸,两天前还塞满了手写的笔记)。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印刷,他平静地回答说:“我需要先研究一下它在越南的实际应用。”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则经常把它拿出来研究,每当我需要比较和理解越南古代诗歌的风格,或者在当地的诗歌俱乐部里用它来辩论韵律和呼应时,我都会拿出来。它就像一套藏书。交通手册过去,它在查找和识别诗歌中的韵律和语音方面非常方便,这正是我在研究作者的语言风格时所需要的。
为了撰写毕业论文,他需要理论基础。因此,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利用自己的俄语技能,翻译了近200页与反向词典相关的资料。这并非所有在战时接受训练的学生都有勇气做的事情。
战后那段时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穷得叮当响。现在回看那时候的照片,每个人都瘦得跟得了肺结核似的。那时,武德义教授每天晚上都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河内20公里去学习喃字。他邀请我一起去,但我懒得去,不想打扰朋友那辆宝贝自行车。我就去了外语学校学了几句法语,然后就“随风而去”了。
他之所以求学,是因为有人赏识他的品质:坚韧不拔、细致认真、一丝不苟、成熟稳重、追求完美,以及渴望自我提升。这位慧眼识珠的老师正是阮泰进教授。然而,他也曾一度在两条道路之间犹豫不决:是选择现代语义学,还是追随两位极其严谨且富有洞见的导师——阮泰进教授和阮丹教授——的历史语言学。当时,两位教授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因此他拥有诸多优势。我对一切都充满兴趣。而他,则终日勤勉地翻译(最初是俄语)语言学文献,耐心地收集着浩如烟海的词汇和历史语法资料。
这本书收录了我当老师第一年翻译的第一批作品。教义导论 语言学作者:Reformatskij。然后大学语言学 艰难的卡塞维奇著(由语言学青年联盟油印出版)。我当时读到这篇文章时,心里想的只有:索绪尔先生已经琢磨这个问题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要创造一个卡塞维奇先生呢?仅此而已。
他日夜钻研阮廌和阮秉谦的喃字诗,令我感到惊讶。但当文章……关于阮廌的诗歌语言(1980年)直到参加语言学会议,我才意识到自己与阮泰干教授同名。此前,我研究的是阮廌,但主要集中于他的思想。读了他的文章后,我才意识到语言学知识在解读文学文本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从此,我对语言学更加着迷。
从那时起,大学教授武德孝很快便在教学界崭露头角,并很快受聘在多所院校任教:河内大学文学院、军事大学外语学院、警察大学、政治军官学校、中央宣传学校……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具备这样的才能。他年轻有为,言辞严肃,有时甚至略显严厉。学生们既敬佩他,又畏惧他。到了二十五岁,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孝爷爷”。
武德义教授在1980年至1983年间的科学著作虽然不多,但进展缓慢而稳定,迅速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研究风格:用证据和事实说话,使用精确的术语,逻辑论证,简洁明了,有效且果断地处理问题或议题。

他曾任语言学系副主任(1996-2000年)和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副校长(2003-2014年)/ 图片:Thanh Long
他没有选择出国留学,而是报读了国内的研究生项目。他一边努力维持生计,一边撰写博士论文。这些词语在含义和辅音方面都有着历史渊源。 越南语中的“头”这看似是一个狭窄的课题,实则需要对语音学、语法、词汇和历史语义学有深刻的理解。当时,他的老师阮德丹教授已移居西贡,也对“语义场”充满热情,并在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精辟的文章。今日知识和新大陆尽管远隔重洋,两人每次见面都会亲切交谈。他的论文导师是两位在语言学领域德高望重的教授:黎光添教授和阮天甲教授,他们既是良师益友,也是同事。阮泰干教授从家中为他提供资料,并指导他查阅图书馆的馆藏,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手工抄写这些资料。
正当我们以为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不得不去金边教越南语——我们称之为“以平民身份上前线”。他带上了所有文件,利用这段时间在蚊帐下撰写论文。当其他人忙着以物易物挣点零花钱时,他却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向当地人请教词语和短语,然后记下来进行比较。晚上停电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词源,和他们争论不休。这很辛苦,但也很有趣。总之,八个月后,论文终于完成,他回到越南答辩。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们不相上下。
那时,他已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受邀在康奈尔大学现代语言与语言学系连续任教三年。一天,我帮他粉刷打扫二楼的房间时,注意到几张薄薄的纸片用回形针夹着,从房间里掉了出来。我捡起来,惊呼道:“这是迪弗洛斯先生的信!”他接过纸片,说道:“哦!不,这不是信。这是教授和另一位先生的评语!我差点就丢了,要是丢了就太可惜了!这是手写的笔记!”我没有抄写下来,而是把它们摘录了下来。
康奈尔大学……1993年4月21日。
摘自 G. Diffloth。致语言委员会。
“Nghia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深受学生喜爱,并且乐于接受建议”……“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并将对他们未来学习越南语大有裨益”(Nghiệu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师,乐于分享自己的观点,深受学生尊敬……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非常有价值,将有助于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越南语。。
J. Wheatley 致 G. Diffloth。
“Nghieu是一位非常称职且尽职的老师……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好的越南语老师。他对语言的细微差别非常了解;他总能想出很棒的对话素材。”Nghieu是一位能力极强、尽职尽责、体贴周到的老师……我认为他是我合作过的最优秀的越南语老师。他非常了解越南语教学中的细微差别,并编写了出色的会话材料。。
他们提交给系主任的两封信也包含了积极的评价和科研合作计划。这显然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内部沟通。系主任非常高兴,立即把信交给了他。每份意见都写满了一整页A4纸。拥有这样一份珍贵的记录,确实令人安心。
他无法逃避管理职责。首先,他担任语言学系副主任。2000年,时任人文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范光龙副教授告诉我:“阮先生从美国回来了,现在有点影响力,应该参与团队管理。你应该试着劝劝他。” 之后,他先后担任科研部主任,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连任两届以上副校长。
他在学校的办公室就像一个专门的图书馆角落,他既在那里处理学业,也在那里准备未来的毕业论文。那就是他的工作。词汇简史 越南语2011年,文章继续定期发表。此外,还出版了合著和个人学术专著;仅在2014-2015年就出版了三部。
重返语言学系从事专业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这很适合我,也让我感到平静,”他说。
武德义教授继承了前辈先驱者的衣钵,成为了一位博学严谨的越南语言学研究者,始终对这项他所投身的艰辛职业充满热情。
他一边啜饮着茶,一边再次说道:“先生,我们一直努力做到善良!”
|
教授、博士。武德义
河内大学文学院。 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语言学系。
语言学系副主任(1996-2000)。 科学系主任(2000-2002 年)。 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副校长(2003-2014)。 比较语言学系主任(2009 年至今)。
|
作者:阮雄薇